

2021年5月25日下午3點,第五屆虬江論壇•第六屆復旦哲學青年教師沙龍在光華樓西主樓2501室舉辦🫎。在本次論壇中🕵🏽♂️,王維嘉分享了他的新著——《優美與崇高🙅♀️:康德的感性判斷力》🛷。我院十多名青年教師和多位碩博研究生到場參加。

閃回
王維嘉從康德“鑒賞無興趣”這一重要命題開始分析:美不在於對象的實存,而在於其形式🥁,即,其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比如🛌🏻,對於一個大三和弦,如果我們只註意其中個別音調對感官的刺激,則我們感到適意。但是👍🏿,如果註意三個音調在想象力表象下的相互關系(即它們所構成的形式)🦢,則我們感到美。
美感如何發生🪺?王維嘉解釋道🙎🏽♀️:在規定性的認識中,想象力組合諸感覺,知性試圖將這些感覺統攝於一個概念📹,判斷力則評判這些感覺是否與概念一致,即,評判想象力與知性是否和諧遊戲👨🏻🦳👩🏽🔧。在鑒賞性的評判中,想象力與知性和諧遊戲,知性卻無法以確定概念來規定諸感覺,因而兩者間發生了自由於概念的和諧遊戲。判斷力對這種自由和諧心態的感性意識🕴🙉,就是美的愉快🧑🏼🍼。
進一步地⛓,既然鑒賞判斷和認識判斷都以先驗認識能力(即想象力8️⃣、知性與判斷力)為基礎,鑒賞判斷就如認識判斷般具有主體間的必然普遍性🌂;換言之,我們假定所有主體都會對同一形式做出相同的鑒賞判斷🧈。但是,不同於認識判斷🧛🏿♀️,鑒賞判斷是感性的👩🏽⚖️👨🏿💼、無概念的🧱,這意味著我們無法證明為何“應當判斷這個形式應是美的”——盡管我們有理由假定“所有人的判斷應當一致”🖕🏽。總之,鑒賞判斷具有一種必然🧑🏻🦼、感性的主觀普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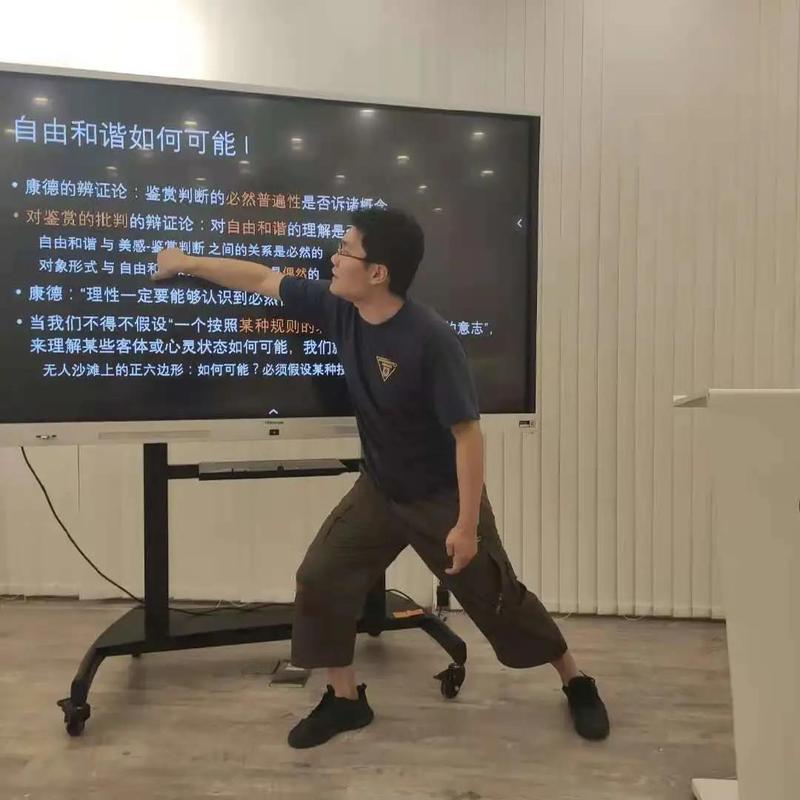
王維嘉主張,康德沒能清楚區分“鑒賞判斷的普遍性的必然性”和“鑒賞判斷本身的必然性”。前者指,所有人都必然地判斷這個形式為美的🙋🏽♂️;後者則指♻,當所有人都判斷這個形式為美的,他們的判斷(作為一個總體)是必然的。康德表面上僅僅關註前者,卻在討論中難免涉及後者🧝♀️,又因其混淆而無法正視它。
康德在“感性判斷力的辯證論”中提出一種二律背反:就其感性的必然普遍性而言,鑒賞判斷是否以概念為基礎?但是👱,在王維嘉看來♓️:《批判》的“演繹論”早已成功證明,鑒賞判斷的必然普遍性決不以概念為基礎🧑🏻🦼;康德的前後矛盾,使得其二律背反無法成立🦗。這矛盾的源頭恰恰是:“辯證論”本應處理鑒賞判斷的必然性,卻錯誤地重訪了鑒賞判斷的普遍性的必然性。鑒賞判斷的必然性預設自由和諧心態的必然性與鑒賞力的必然性⏳,而自由和諧的必然性問題會引發一種真正的二律背反。王維嘉提出,自由和諧對於我們是偶然的🍋🟩,但是,在我們的設想中👏🏿🧑🏻🔧,這種心態可能對於另一種智能是必然的——那個智能總是能通過一個“連續序列”的理念來證明一個形式如何必然引起和諧心態,而我們卻受製於自身的感官性條件♣︎、無法在直觀中展現那個理念🚣🏼♂️。
基於對康德崇高論的研究,王維嘉區分了想象力崇高和感官崇高🧑🏻🎓,並進一步將前者分為數學崇高和物理崇高🐱,將後者分為自由崇高和自然崇高📺。有些人努力克製自己的感官沖動(比如苦行僧),並不明確出於道德法則,而只是為了體證“我可以那樣(或不那樣)做”的一種欲求能力的消極自由——他們因此感到自由崇高。相反,當一個人盡全力克製其沖動、卻仍然失敗了(比如溺水時忍不住呼吸),他既將身體視為超出自己控製的自然物👭🏻,又仿佛感到這一自然物的理知性因果性,即,仿佛感到自然背後的某種自由意誌——這就是王維嘉所謂“自然崇高”的體驗。王維嘉承認,這些重構和拓展超出了康德哲學本身,並有待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報告之後,青年教師們進行了約一個小時的熱烈討論。陳佳問到了《判斷力批判》的定位➿。王維嘉回應:雖然此書確實包含鑒賞論、並因此被許多學者理解為一本“美學著作”🧎🏻♂️,它其實旨在解決前兩大“批判”的遺留問題🍾,即,達成理論哲學與道德哲學(或自然領地與道德領地)之間的過渡。《純粹理性批判》回答了“我們能知道什麽”🧜,《實踐理性批判》回答了“我們應當做什麽”🧑🏼🚀,《判斷力批判》則試圖回答“我們可以希望什麽”,即🟠,(我們所應當追求的)最高善能否在(作為我們認識對象的)自然中得到實現🧑🏿⚕️。所以,盡管《判斷力批判》確實包含美學部分、並在美學史上舉足輕重,卻不宜被稱為一本“美學著作”。
此外,徐波質疑康德所謂“鑒賞判斷的主觀普遍性”。王緯提醒王維嘉註意區分“inferential necessity”與“causal necessity”。孫寧指出,王維嘉有萬物有靈論傾向,並得到後者認可🧚🏼♂️。謝晶主張,王維嘉將合目的性與道德等價了🔤。王球、何益鑫分別就數學美和醜感提問。
文案:王維嘉 杜博文
圖片💗👰♂️:於明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