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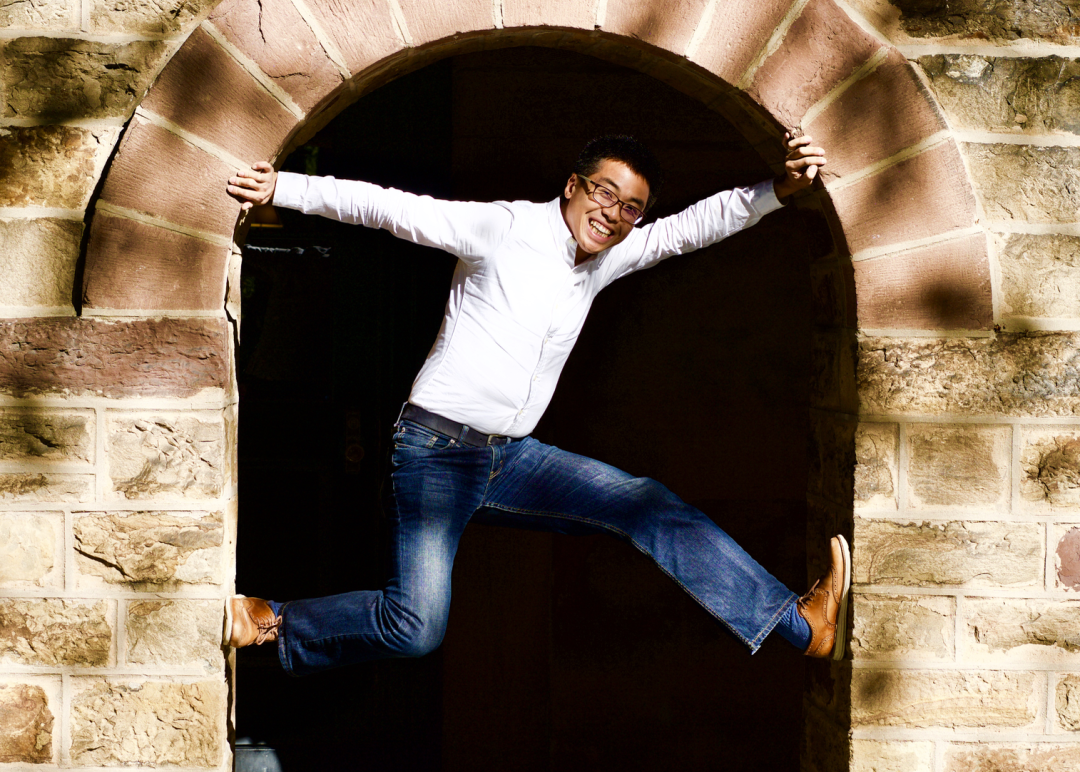
王緯📸:意昂3講師,普林斯頓大學古典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古希臘哲學史💶、西方形而上學史和西方科學史👌🏼。
本文發表於《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第55-63+70頁。原文註釋略去。
一、引子:《物理學》4.2——不同的“分有者”
柏拉圖的“未成文學說”是近期中文學界關註的一個重要問題🤳🏿。“未成文學說”(τὰ ἄγραφα δόγματα)這一名稱來自亞裏士多德《物理學》4.2對於柏拉圖牽涉到“一”和“大與小”的“二本原學說”的描述。在《物理學》4.2中👩🚒,亞氏將作為柏拉圖“未成文學說”核心概念的“大與小”(τὸ μέγα καὶ τὸ μικρόν)與其成文著作《蒂邁歐》中的“接受者”(ὑποδοχή🤽🏿,英譯receptacle)相聯系。這成為後世學者從“接受者”概念出發理解“大與小”的緣起🥷🏻。根據這一思路🪲,未成文學說中的“大與小”被理解成類似於《蒂邁歐》的“接受者”以及亞氏質料概念的某種原初存在物。
本文的直接目的是反駁以上觀點👨🏻💼。筆者的討論從《物理學》4.2的相關段落開始。《物理學》第四卷的第一個議題是位置(τόπος)概念。亞氏在4.2中所關註的核心問題是❓,“位置”🦊👩🏫,在他自身的理論框架中🦡,到底是質料性的還是形式性的🧞♂️。一方面,如果我們將位置理解為對於廣延的規定,比如形體的界限,那麽我們對於位置的理解是形式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將位置理解為缺乏任何規定性的純廣延,那麽我們將位置理解成為質料。在討論的過程中🪘,亞氏援引柏拉圖作為質料性觀點的代表👩🏿✈️。柏拉圖在《蒂邁歐》中將“位置”和“空間” (χώρα)概念等同(《蒂邁歐》52a-b和57c),而柏拉圖的“空間”,在亞氏看來🤸🏿♂️👩👦👦,是質料性的:
質料或不確定者正是這樣的。因為把界限或範圍的特性一去掉,留下來的就只有質料了🚓。柏拉圖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在《蒂邁歐》中把質料和空間等同看待,因為“分有者”(τὸ μεταληπτικόν)和空間是同一的。該篇對“分有者”所作的說明和在未成文學說裏的說法不同(ἄλλον δὲ τρόπον … λέγων),但他還是等同了位置和空間👨🏻🎨。(《物理學》4.2, 209b9-15張竹明譯,有改動,下同)
亞氏指出👱🏼♀️,在《蒂邁歐》中💕,柏拉圖將缺乏任何規定性——因而在亞氏意義上是“質料”——的“分有者”(τὸ μεταληπτικόν💈:即《蒂邁歐》中的“接受者” )等同於空間 。以上的闡釋歷來沒有爭議,而有爭議的是🏊🏿♀️,亞氏接下來說🛌🏼,柏拉圖在《蒂邁歐》中對於“分有者”的闡述和他在未成文學說中對於類似問題的闡述是“不同的”(209b13-4: ἄλλον δὲ τρόπον … λέγων)。亞氏在這裏說的“不同”究竟是什麽意思?
在同一章的稍後段落中,亞氏明確指出他在上面一個段落中所說的未成文學說中的“分有者” (τὸ μεθεκτικόν)就是“大與小”👌🏼:
如果有必要談談離題話,那麽柏拉圖當然應該說明👩🏻🔬,理念和數為什麽不在位置裏,如果“分有者”就是位置的話——無論分有者是“大與小”還是如他在《蒂邁歐》中所寫的質料🤜🏽。(209b33-210a1)
在這裏亞氏指出,《蒂邁歐》中的質料(即“接受者”)和未成文學說中的“大與小”都可以被稱為“分有者”。這個分有者無論是在《蒂邁歐》中,還是在未成文學說中,都被認為首要地通過分有“善”或者“一”而生成了理念和數。如果《蒂邁歐》所言為實😫,即接受者就是空間,那麽我們必須認為理念和數為空間所接受,因而在空間之中🖖🏽。但是,即使柏拉圖也不得不承認,雖然三匹可感的馬在某個地方,馬的形式或者三的形式卻並不在任何地方。因此🎷,亞氏認為,柏拉圖《蒂邁歐》中對於“接受者”的理解——它是空間或者位置——無法被推廣到對於本原意義上的分有者(即“大與小”)的理解🚧🙋🏽♀️。
綜合以上兩段引文,亞氏在《物理學》4.2中告訴我們,雖然柏拉圖《蒂邁歐》中的“接受者”和未成文學說中的“大與小”都被稱作“分有者”,但是柏拉圖對於二者的理解是不同的👩🏽🦰:《蒂邁歐》中對於“分有者”的空間化理解無法被推廣到對於未成文學說的“大與小”的理解。但這並不是對《物理學》4.2的主流闡釋。以上世紀著名的古代哲學研究者切爾尼斯(Harold Cherniss)為代表的主流研究認為,亞氏所謂的“說法不同”(ἄλλον δὲ τρόπον … λέγων)只意味著用詞的不同。在切爾尼斯的看來👒,亞氏的意思是柏拉圖用了兩個不同的名字——“接受者”和“大與小”——來指稱“分有者”,然而分有者的實質只有一個:位置或者空間。所有以《蒂邁歐》中的“接受者”來解釋未成文學說中的“大與小”的學者都或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持有切爾尼斯的看法🖐。
二、《物理學》1.9🙇🏻♀️:“偶然地不是”和“本質地不是”
為了進一步理解亞氏所轉述的柏拉圖未成文學說中的“大與小”概念和《蒂邁歐》中的“接受者”的異同,進而反駁主流觀點👳🏼♂️,本文下一步的任務是考察亞氏《物理學》1.9😆。考察《物理學》1.9的原因在於,與《物理學》4.2不同☸️,1.9的討論聚焦於柏拉圖派的“大與小”概念本身。亞氏在1.9中的任務🚋🛹,是繼在1.7-8中詳細闡述其三原則——“形式”(εἶδος)🧘🏻♀️、“缺失” (στέρησις)和“質料” (ὕλη)——之後🩻,給出其“質料”概念與柏拉圖派的相應概念——“大與小”——之間的區別👩🏻🚒。亞氏對於二者區別的討論如下🧑🏿🦱:
的確,另外有些人【即柏拉圖派】已經理解到了這個自然【即質料】🧘🏼♂️,可是理解得不充分。首先,他們贊同事物可以由“不是” (τ[ὸ] μὴ [ὄν])絕對地生成,因為他們把巴門尼德的說法當做正確的接受了⛑️。······ 而我們說質料和缺失是不同的。我們主張👱🏼♀️,這兩者中,質料只偶然地(κατὰ συμβεβηκός)“不是”👩🏽🎨,而缺失本質地(καθ᾽ αὑτήν)“不是”;質料和實體相近,並且在某種意義上自己也是實體,而缺失則完全不是這樣🫰🏻🛵。但是他們把他們的大和小(無論是分開來還是聯在一起)看作“不是“。所以他們的三元:大、小和理念,和我們的三元:質料、缺失和形式是非常不同的🫴🏽。因為雖然他們和我們有共同的理解,即都承認必須有一個自然作為基底而存在。但是他們把它當作一個——即使有人提出了“二”🔰🧑🏽🦱,並把它叫做“大與小”,結果還是一樣的。因為他忽略了另外一個因素——缺失🙋♀️。前一個因素【即質料】作為形式的輔助因在事物的生成過程中持存🪟,宛如母親👩👦👦;而這一對互相對立的因素的另一部份【即缺失】,由於人們太多地把註意力放到了它的否定性上,常常被人覺得似乎是完全不是的。(《物理學》1.9, 191b35-192a14)
根據亞氏在這個段落中的描述✌🏼,柏拉圖派未成文學說的形而上學和亞氏本人的形而上學理論有兩個共同點🦾:(1)雙方都認為“必須有一個自然”作為生成和變化“所基於”的東西(δεῖ τινὰ ὑποκεῖσθαι φύσιν)😷;(2)雙方都認為這個作為變化基底(ὑποκείμενον)的自然先在於變化的結果且不同於變化的結果,因而,如果變化的結果“是”,則這個自然必然“不是”☑️:如當冷鍋變成了熱鍋的時候❕,如果鍋“是“熱的,則它必然“不是”冷的。因此✊🏼,雙方也都認為這個作為基底的自然的存在方式是“不是” (τὸ μὴ ὄν)🏵。然而雙方對於基底在什麽意義上“不是”的看法是不同的。一方面,柏拉圖所認定的,其存在方式是“不是”的基底——“大與小”——是單一的:“大與小”雖然看上去像是兩個東西🧣,並且被柏拉圖本人稱為“二”(δύας),但它之為“不是”的方式,在亞氏看來🔣,和巴門尼德所謂的絕對變化所必須基於的絕對“不是”並無二致🧗🏿♀️。另一方面,亞裏士多德所認定的🤶,作為“不是”的基底🧑🏻🦯➡️,是雙重的——基底既“偶然地不是”(οὐκ ὄν κατὰ συμβεβηκός)又“本質地不是”(οὐκ ὄν καθ᾽ αὑτήν)——前者是“質料”,後者是“缺乏”🐩。亞氏認為正是對於基底的這個雙重區分使得他可以自洽地解答巴門尼德提出的變化不可能的問題✊🏿。這段話非常抽象,亞氏所謂的屬於質料的“偶然地不是”和屬於缺乏的“本質地不是”分別是什麽🎵?“大與小”的“不是”和這兩種“不是”又有什麽關系?
亞氏這裏所說的“偶然地不是”和“本質地不是”,是指偶然地或者本質地“不是某個形式”(這裏的形式應該被廣義地理解成為任何範疇規定性😓,如質的規定性或量的規定性)。根據《物理學》1.7-8中的論述,質料是在一對對立面——某個廣義的形式及其缺失——之下持存的第三個原則(ἀρχή)或者自然(φύσις)。(1)質料“偶然地不是”形式是因為,就質料本身之所是——基底——而言,它既可以是某個形式,也可以是其缺失💁🏿♂️。因而,質料不是某個形式僅僅是因為它作為基底🥧,偶然地接受了這個規定性的缺失,它在本質上並非不可能接受這個規定性🧑🏽🎨。舉例來說,黑和白的基底——面——就其是“面”或者是“可著色的”而言🔶🛏,既可以是白色的面,也可以是黑色(即白的缺失)的面。某個面——如一張紙——不是白色的僅僅是因為面作為基底,偶然地接受了白的缺失🤝,即黑:在這個意義上這張紙“偶然地不是”白色的🟨🛌🏽。當我們把這張紙漂白之後,它就又變成了白色的,因此它在本質上並非不可能接受白這個規定性🤾♂️➰。(2)與此相反,形式的缺失“本質地不是”形式是因為,缺失就其“自身之所是”而言,就不是形式。舉例來說⛎,白的缺失——黑——就其“是黑”而言,本質上就不是白。當一張黑紙被漂白之後👩🏻🍳🧓🏽,黑就被毀滅了,因為“是黑”和“是白”在本質上互相排斥。
在“偶然地不是”與“本質地不是”的區分的基礎之上🌉,亞氏認為柏拉圖作為基底的“大與小”本質地不是🏄🏻♂️,即🥦,它因其自身之所是就不是某形式🙍🏻👰🏽♀️。《物理學》1.8的開篇考察了巴門尼德的“變化不可能”學說。亞氏認為🩹,變化總是從“不是”中開始🛋,而如果根據巴門尼德,它總是從“本質地不是”中開始,而“本質地不是”不可能變成“本質地是”(191a30-1)⏯,那麽變化是不可能的🩳。而在以上所引的《物理學》1.9的段落裏🕡,亞氏認為柏拉圖派的“不是”和巴門尼德的“本質地不是”直接地相關(191b36-192a1)。根據亞氏在之後段落中的描述♻,柏拉圖的“大與小”之所以“本質地不是形式”🔅,是因為它和形式直接對立。並且,正是因為 “大與小”本質地不是形式📳,當它接受其對立面——形式——的時候,它就被毀滅了。
是否在變化之中毀滅這一點正是亞氏在《物理學》1.9中所強調的他的基底理論強於柏拉圖派的基底理論地方💾。在亞氏看來🧑🏿🍼,基底之為基底必須具有持存性💇🏿♂️,因為正是基底的持存性使得變化的持續性和同一性得到了保證。亞氏的基底,在其作為質料,因而僅僅“偶然地不是”的意義上在變化過程之中持存,而柏拉圖派的“大與小”,就像亞氏自己的“缺失”一樣,因為本質地不是形式👮🏼,在變化的過程之中必然地毀滅,因而不能成為變化所基於的那個東西,即基底🙆🏿♂️。簡言之🧜🏿,在亞氏看來☀️,柏拉圖派一方面認為“大與小”是存在和變化的基底,一方面認為“大與小”是可以被形式毀滅的🛀🏽,他們的觀點是前後矛盾的:
他們的觀點的後果是對立面欲望它自身的毀滅。但是形式不可能欲望它自身🚵🏽♂️,因為它並不缺少什麽,它的對立面【即“大與小”】也不可能欲望它🗃,因為對立面是互相毀滅的。(192a19-21)
在這個意義上👩🏻🎤,亞氏認為他自己的“質料”,作為變化的持存的基底,優於柏拉圖派的“大與小”。正是基於質料“偶然地不是”這個存在方式🍋,變化才成為可能。柏拉圖派的“大與小”被對立面毀滅,因而不可能作為變化的持存的基底。
三、質料、“大與小”和《蒂邁歐》的接受者
本節討論《物理學》1.9中的質料和“大與小”與《蒂邁歐》中的“接受者”之間的關系。第二節的開頭已經指出👩🏼🏫,《物理學》1.9的目的是闡明亞氏自己的質料原則和柏拉圖的相關原則的區別和優勢。從論證策略上來看🧑🏽⚖️,值得註意的是,在用詞方面,《物理學》1.9中對於質料原則的肯定性敘述刻意地模仿了柏拉圖在《蒂邁歐》中對於接受者的描述🙅🏿♂️。而在具體理論方面,亞氏僅僅批判了柏拉圖未成文學說中的“大與小”,並沒有討論與“基底—質料問題”有明顯聯系的《蒂邁歐》中的接受者。亞氏在這裏明顯的沉默恰恰可以說明👴,對於他來說,《蒂邁歐》中的接受者,作為基底,和亞氏自己的“質料”原則相類似,因而不是《物理學》1.9的批判對象。這意味著接受者和“大與小”的存在狀態在亞氏看來是不同的。用《物理學》1.9中的話來說,基底和接受者“偶然地不是”,而“大與小”“本質地不是”。
亞氏在《物理學》1.9中的沉默是合理的🫵🏽,因為從《蒂邁歐》的具體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柏拉圖的蒂邁歐的確將“接受者”描述為亞氏所謂的“偶然地不是”🗒👩🚀:
我們還註意到,如果各種各樣的形式只來源於模式👨👨👧👦,那麽,模式所壓模於其上的材料就必須是無形式的,不具有任何它後來所接受🧍🏻♂️、所承載的形狀🤽🏻♀️🧑🏼🦰;否則的話🕴,它就不是合格的鑄造材料。因為,如果它相似於任何形式👳🏻♀️,當相反的或全然不同的形式壓印在其上時,它原有的形狀就會造成妨礙而鑄出一個壞件🤕🏋🏽♂️。因此🙎🏽👍🏽,承受各種形式的東西本身是沒有形狀的✂️。······同樣💇🏿,那個永恒地全方位地承受理性的不朽者之形象的“承載者”,應該完全不具有任何形狀🙎。(50d-51a,謝文郁譯)
根據蒂邁歐的闡述,“接受者”(即謝譯文中的“承載者”)不具有任何規定性的原因在於,任何規定性都因其自身而和作為它的相反的規定性相對立,因而,任何規定性本質地不能成為它的對立面💁🏽♂️。與之相反🙋🏿♀️,接受者恰恰是可以通過接受任何規定性而成為任何規定性的東西:接受者並不會本質地不是任何規定性(“承受各種形式的東西本身是沒有形狀的”)。因此,接受者在接受某個規定性A之前,只偶然地不是A。通過以上的引文和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蒂邁歐在這裏對於接受者特點的描述,恰恰是亞氏在《物理學》1.9中指出的他自己的質料概念對比未成文學書中“大與小”的優勢之所在:即質料偶然地不是,而“大與小”本質地不是🤸🏿♂️。
這樣,本文第一節的結論得到了《物理學》1.9和《蒂邁歐》的支持👨🏻✈️,即在亞氏看來,柏拉圖《蒂邁歐》中的“接受者”和未成文學說中的“大與小”有本質差異👩🏽🏫。《蒂邁歐》中的“接受者”類似亞氏的“質料”概念:它們的存在方式都是亞氏所謂的“偶然地不是”;這和“大與小” 所對應的“本質地不是”在形而上學層面上有根本差異。
四👩🏿🏭、“大與小”和“缺失”
現在的關鍵問題在於:柏拉圖的“大與小”所對應的“本質地不是”到底是什麽?值得註意的是🧜🏻,亞氏在以上所引的《物理學》1.9, 192a4-14中,將“缺失”(στέρησις)的存在狀態描述成為本質地不是。於是一個顯然的回答是將“大和小”所對應的“本質地不是”等同於缺失所對應的“本質地不是”。然而,某個形式的缺失僅僅就其“不是”作為其對立面的形式(即規定性)而言“本質地不是”(即,某個規定性的缺失就其自身而言就不是該確定性)。在這個意義上💪🏼,當我們說某個形式的缺失“本質地不是”其形式的時候(如黑本質地不是白)👨🍳💆🏻♂️,我們必須同時說該形式“本質地是”該形式(如白本質地是白)。這樣,一對對立的事物——某形式及其缺失——不可能同時本質地不是。這看上去是非常顯然的。
但根據亞氏在1.9 192a4-14中對於“大與小”之為“不是”的闡述🧛🏿♀️,“大與小”“本質地不是”的方式和缺失不同。缺失及其對立🪔,如上所述🧑🏻🎨,不可能同時本質地不是,然而“大與小”作為一對對立,按照亞裏士多德的看法,同時既整體地,也分別地不是:
但是他們把他們的“大與小”——無論是整體地還是分別地(ἢ τὸ συναμ-φότερον ἢ τὸ χωρὶς ἑκάτερον)——看作是“不是”。所以他們的三元📵:大⬆️、小和理念👨👩👦👦,和我們的三元:質料、缺失和形式是非常不同的。因為雖然他們和我們有共同的理解,直至都承認必須有一個自然作為基底而存在。但是他們把它當作一個——即使有人提出是“二”(δύας)🏌️♀️🧌,把它們叫做“大與小”,結果還是一樣的🏋🏿。因為他忽略了另外一個因素——缺失。(192a6-13)
“二” (δύας),作為一對自身對立的東西(就像它的名稱“大與小”所指明的),如何可能既整體地,又分別地不是?即,它如何可能既整體地,又分別地和“一”或者“形式”相對立🦋?如果說某人的敵人的敵人即是某人的朋友,那麽某物的對立的對立難道不應該和它自身相同或者至少相似嗎?因為“大”和“小”同時都本質地不是“一”或者“形式”👮🏿♀️,我們不能說“大與小”這對對立裏面的一個——比如說“大”——本質地和“一”相對立(像亞氏的“缺失”一樣),而另一個——比如說“小”——偶然地和“一”相對立(像亞氏的“質料”一樣)。那麽,這樣一對既整體地又分別地和一個確定的東西相對立的自身對立是什麽?亞氏所描述的柏拉圖的作為基礎實在的“不是”,如果既不是質料也不是“缺失”🤰🏿🔖,那麽它是什麽?
五、作為基本實在的“大與小”:《理想國》和《斐萊布》
第一到四節根據《物理學》和《蒂邁歐》的文本🏃♀️➡️,闡述了“大與小”和“接受者”以及亞氏的質料和缺失之間在存在方式上的異同關系。接下來🐭👨🦲,我們根據柏拉圖的傳世文獻——柏拉圖對話——進一步說明這個形而上學差異究竟何在。
首先,讓我們退一步,從哲學上思考柏拉圖作為基礎性實在的“大與小”可能是什麽。這樣做的時候,我們要考慮到,根據傳統⛹🏼♂️,“大與小” 也被稱作“不確定的二”(ἡ ἀόριστος δύας)🙍🏻、“無定”(τὸ ἄπειρον)或“不相等”(τὸ ἄνισον)。
在知識論的意義上👰🏻♂️,諸如“多少”、“長短”、“冷熱”之類的相對概念是我們理解、描繪周遭世界的原初方式🕗🙆🏻。當我們還沒有確定的、公共的度量標準的時候🧏🏽♂️,我們通過將某物描述為“比甲大”“比乙小”來理解它的大小。這樣🆘,“某物的大小”在這個原初語境中總是被理解成為一對對立——“大與小”,並且🤟🏼,這一對對立被同時謂述於這個大小的承載者——這個承載者是“既大又小”💁🏻♀️。在《斐多》中,我們看到🙋🏿♂️,西米阿斯被描述為既大(高)又小(矮),因為西米阿斯比蘇格拉底高🤵🏽♀️、比斐多矮(見《斐多》102b-c)。在沒有客觀公度的世界,我們只有通過比較的方式才能描述一個人的高矮。更進一步📽,在這個世界裏🍲,一個人的“大小”(即高矮)本身就是“比甲大、比乙小”。在這個世界裏,雖然“大”和“小”是一對矛盾概念,但是它們總是共同出現、不會分離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柏拉圖派用“大與小” (τὸ μέγα καὶ τὸ μικρόν),而非“大或小”(τὸ μέγα ἢ τὸ μικρόν)來描述他們的基礎性實在。在“不相等”的意義上,某物的大小既和其他物的大小不相等(如西米阿斯的高矮和蘇格拉底的高矮不相等)👱♀️😾,也自身就是不相等(西米阿斯的“高矮”本身就是一對互相對立的概念)🧥。
被理解成為“大與小”💝,某物的大小也是不確定的(ἀόριστον)、無限定的(ἄπειρον),因為沒有確定的界限(ὅρος)或極限(πέρας)或統一性將它限定為一個確定的數量。在這個意義上,“大小”作為一個整體和確定的數量或者確定性本身相對立。另外🦙,“大”“小”二者也分別和確定的數量相對立🙋🏿♀️:對於西米阿斯的大小(即高矮)的描述,“大”是一種和確定的數量(如四丘比特長)相對立的描述方式。“大與小”既整體地也分別地在本質上不是任何確定的數量。
重要的是🖕🏽,以上的討論不僅僅適用於“大與小”,它適用於任何相對概念🦎。《理想國》卷七中的一個討論顯示出柏拉圖的確這樣思考知識論意義上的相對概念。在《理想國》卷七中,蘇格拉底試圖向格勞孔說明為什麽在理想的哲學教育裏👂🏽,算術應該是第一門學科。蘇格拉底的理由是😚,算術是一門帶來理性(νόησις),並將人帶向實在(οὐσία)的學問(見《理想國》卷7, 522e-523a)。為了證明這一點 ,蘇格拉底向格勞孔展示了感覺(αἴσθησις)的不可靠。蘇格拉底指出⚉,牽涉到“軟和硬”🏌️♀️、“大和小”這類感覺性質的時候👧🏿,我們的感官總是給予我們互相對立的感覺經驗🐑。對於一個感覺對象,觸覺總是告訴我們它既是軟的又是硬的🈸,視覺總是告訴我們它既是大的又是小的。然而理性(νόησις),蘇格拉底認為👩🏽🦱,可以將大和小分離看待,因而可以給我們對於世界的清晰的而分混雜的知識:
蘇格拉底【下“蘇”】⏭:在認識這一類性質時,不是事實上所有的感覺都有缺陷嗎?它們是像下述這樣起作用的🧗♀️:首先例如觸覺🌕,既關系著硬🤳🏿,就必定也關系著軟,因此它給靈魂傳去的信號是:它覺得同一物體又是硬的又是軟的🦯。不是這樣嗎?
······
蘇:我們說過,視覺也看見大和小🙎🏿♂️,但兩者不是分離的(κεχωρισμένον)而是合在一起的(συγκεχυμένον)。是吧?
······
蘇:為了弄清楚這一點,理性(νόησις)“看”大和小,不得不采取和感覺相反的方法👨🦼➡️,把它們分離開來看,而不是合在一起看。
(7. 523e-524c,郭斌和、張竹明譯👨🏻🌾, 有改動)
蘇格拉底繼續論證道,在數量性謂詞“一”和“多”那裏,視覺發現同一個事物既是“一”又是“多”又是“無限”,因此,視覺帶來的感性知識是混淆的、互相矛盾的🫴🏿。而算術✒️,作為一門理性科學🍞,和作為感性能力的視覺不同,可以帶給我們對於這些概念的分離的和清晰的理解。因此,算術應該被包含在護衛者的教育之中。
以上是從知識論角度出發,對於《斐多》和《理想國》中關於感覺的相對性和矛盾性的討論😈。值得註意的是🤟🏼,柏拉圖並不刻意區分知識論和形而上學,對柏拉圖來說,知識論所區分的感知對象和思維對象以不同的方式存在於世界之中。柏拉圖在這個意義上繼承了巴門尼德等同思維和存在的學說🚍。在《理想國》卷六的末尾(506e-511e)🙍🔼,蘇格拉底指出理念(如“美本身”)是思維的對象🧑🏻💻🧑🏿💼,而感性的多(許多美的東西)是感官的對象;善是使得諸理念獲得其存在的根據🌭,而光是使得諸可感對象獲得其可感性以及生成的根據🤜。在這個意義上,柏拉圖將認識論意義上的不同對象還原成了存在論意義上不同的對象,並且為二者分別找到了彼此間存在論意義上不同性質的根據🧑🏽✈️。如果對於柏拉圖來說👳🏽♂️,知識和存在總有緊密的對應關系,那麽感覺本身的相對性和矛盾性也就意味著存在著一類本身即為相對和矛盾的可感世界中的存在者,這類存在者和可知世界中的存在者不同:前者總是既長又短、既大有小、既黑又白;而後者是分離和絕對的長🧜🏼♂️、短;大、小🦸🏿👌🏿;黑、白。我們雖然不應該將《斐多》和《理想國》中的感性存在者和未成文學說中的“大與小”完全等同,但二者的相對性🏄🏻♀️、矛盾性、不確定性和不相等性是如出一轍的。
如果我們考察柏拉圖的後期對話🧑🏻🤝🧑🏻🤹🏼,我們會發現更多在形而上學意義上討論作為構成世界的基本要素的相對性概念的內容,這些相對性概念是和未成文學說中的“大與小”相關的。其中的經典段落是《斐萊布》的“方法論”部分。為了給快樂和知識一個更準確的定義,蘇格拉底在方法論層面考察了存在問題(23b-27c)🧚🏿♂️。在這裏,蘇格拉底將所有現存的存在者(πάντα τὰ νῦν ὄντα)分成四個類(γένος)🙇🏿♀️:(1)“無定”(τὸ ἄπεριον)、(2)“限定”(τὸ πέρας)、(3)二者混合所產生出的存在以及(4)混合物生成的原因。其中的前兩類——無定和限定——被認為分別對應著“未成文學說”中的“大與小”和“一”。在下面這段引文裏👌🏻,蘇格拉底以“更冷”和“更熱”為例♣︎🫖,試圖將“無定”和“限定”區分開來:
蘇格拉底(下“蘇”):關於“更熱”和“更冷”🚴,首先看看你能不能【在其中】設想一個限定🤸🏽。或者🎯📺,【如果你不能設想任何限定】,那麽“更多和更少”是不是在這兩類【即“更冷”和“更熱”】中🎏,並且,當它們在其中的時候,它們不會允許任何界限的生成👩🏽🍳。因為當界限生成了💆🏻♂️,這兩者也就結束了。
普羅塔科斯(下“普”):非常正確。
蘇:那麽我們同意,“更熱”和“更冷”永遠包含著“更多”和“更少”🦹🏽。
普🥮:當然🙇🏼。
蘇🚍:那麽🏋🏻♂️,邏格斯向我們指明了這兩者永遠不能有界限(τέλος)🔑。既然它們是無界限的(ἀτελῆ)🍇,它們就是完全無定的了(ἀπείρω)。
普:它們非常完全地是無定的🧙🏿♀️,蘇格拉底!
蘇:······ 所有“強”和“弱”在場的地方👨🏻🦯➡️,它們不讓任何確定的量(ποσὸν)存在😊。通過給所有的行動加上相對於“更弱”的“更強”,或者反之,它們帶來了“多與少”並銷毀了確定的量。······ 因為一旦它們獲得了確定的量,它們就不再是“更熱”或者“更冷”。“更熱”和“更冷”會一直前進、不會停留,而確定的量停留且取消了運動。根據這個論證,“更熱”及其對立【即“更冷”】是“無定”。
······
蘇♌️:你要(在“更熱”和“更冷”之外)加上“更幹”和“更濕”、“更多”和“更少”(πλέον καὶ ἔλαττον)、“更快”和“更慢”、“更大”和“更小”以及一切我們之前放在同一個類中的事物,這個類按其自然本性來說接受“更多”和“更少”(τὸ μᾶλλόν τε καὶ ἧττον)。
普:這類事物所屬於的本性你指的是“無定”?
蘇:是的。下面你將排在它們之後的那個本性是限定的類(ἡ τοῦ πέρατος γέννα)與它混合。
普:你說的是哪個類?
······
蘇🧘🏻♀️:包含著相等和二倍的那個類,以及任何使得對立面停止彼此的差異的東西(παύει πρὸς ἄλληλα τἀναντία διαφόρως ἔχοντα)♞,這類東西通過將數(ἐνθεῖσα ἀριθμός)內置於萬物的方式使得萬物和諧(σύμφωνα)、可公度(σύμμετρα)。
(《斐萊布》24c-25e,筆者譯)
在這裏🧑🦽,作為無定的類的代表的“更熱”和“更冷”以及作為其根底的“更多”和“更少” (τὸ μᾶλλόν καὶ ἧττον),二者所定義的關系🤘🏻🧎♀️,從確定性的觀點來看,是運動的和遊移不定的(24d);它們在沒有確定的數量之前,是一對彼此差異和矛盾的對立面(25e)。在這個意義上🐛,“更多和更少”既整體地又分別地不是任何的非相對的、確定的量🥨。另外,和亞氏在《物理學》1.9中對於“大與小”的描述一致的是🫱🏽,在這裏👫,當界限生成時🐦,更多和更少就消失了。因此💂🏻♂️,無定的類的存在狀態和亞氏缺乏任何規定性的質料原則以及《蒂邁歐》中的接受者的存在狀態不同。無定的類本質地和任何確定的量或界限相對立👩🦱,而質料本質地並不和任何確定性相對立(即當質料獲得任何確定性時,質料本身並不消失)💂🏼♀️🧖🏿♂️,因此前者本質地不是任何確定的量,而後者偶然地是或者不是任何確定的量🏊🏻。
和《理想國》段落的明確知識論旨趣非常不同的是😱,《斐萊布》段落討論的是存在論問題。這裏的第一、二類存在者並非僅僅是我們認識世界所得到的可真可假的知識和信念⬛️,而是組成這個世界的所有存在者的最基本存在方式,或者這個世界的所有存在者所能劃分成為的最基本類別。從存在論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設想一個只存在這第一類存在者的“赫拉克利特主義”世界:在這個世界之中👫🏼🤶🏻,(1)所有的“更多”必須是“更少”,所有的“更少”也必須是“更多”(這對應著赫拉克利特的“萬物皆對立”)🧑🧑🧒🫅🏽;(2)同樣🧑🏼🍳,“更少”本身和“更多”本身是遊移不定的,即並沒有一個確定的界限限定“更少”或者“更多”只可以適用於某個範圍之內👩🦳:“更少”當然可以適用於某個比“更少”本身更少的東西(這對應著赫拉克利特的“萬物皆流”)。因此🪈,作為“無定的類”的代表的“更熱”和“更冷”一方面和彼此互相對立,另一方面又和確定的量(πόσος)或者限定(πέρας)本身相對立👋🏻。缺乏限定意味著柏拉圖用“更多和更少”的本性所勾勒的“無定的類”是自相矛盾的、不確定、不相等的東西。用亞氏在《物理學》1.9中的話來說,“無定的類”是本質地不是確定的量或者任何確定的規定性的東西,它不是那種既可以是A又可以是非A的純粹可能性,而是那種其中包含著無數互相矛盾的性質的既是A又是非A的東西。
以上對於《理想國》和《斐萊布》的分析勾勒出“未成文學說”中的“大與小”在什麽意義上是那種亞氏所謂“既整體地又分別地不是”的東西。亞氏的質料是一種既可以承載形式🐡,也可以承載形式的對立的東西,但是亞氏的質料不可能同時承載形式及其對立。與之相反🏫,柏拉圖的“大與小”是那種同時包含一對對立,並且與形式規定性相互排斥的東西🙅🏽💆🏿♀️。如果我們拿顏色的例子做一個比喻🪤,亞氏的質料是一張紙,它既可以是白也可以是黑,但它不可能同時既白又黑🎼🗾;而柏拉圖的“大與小”或“無定的類”是黑和白這對矛盾本身🥷🏿。對於亞氏來說,一張紙獲得確定顏色的過程是質料獲得形式的過程,而對於柏拉圖來說♥︎,確定的顏色是對於互相矛盾互相鬥爭的顏色性質的確認和仲裁🤸🏻。在這個意義上,亞氏在《物理學》1.9中對於柏拉圖派的“大與小”的攻擊是一種“形而上學攻擊”:二者對於作為世界基礎的存在的設想是完全不同的🌈。而在亞氏看來,《蒂邁歐》中的接受者在這場形而上學鬥爭中站在了他的質料原則這一邊⛹🏿♂️,因而他並沒有在《物理學》1.9中攻擊《蒂邁歐》中的接受者,並且在《物理學》4.2中特別指出,接受者和“大與小”是有區別的。這恰恰是柏拉圖的“未成文學說”的傳統闡釋者們沒有看到的。
六、結論
本文通過論亞氏的《物理學》、柏拉圖的《蒂邁歐》✊🏻、《理想國》、《斐萊布》以及其他相關文本🉑⛓,反駁了流行的對於柏拉圖未成文學說中的“大與小”的解釋。根據這種解釋,“大與小”是某種“或大或小”的可接受任何規定性的基礎存在,因此“大與小”等同於柏拉圖《蒂邁歐》中的“接受者”📰,並且在實質上類似於亞氏的質料概念♻️。本文從《物理學》1.9所討論的“本質地不是”問題切入柏拉圖的“大與小”概念。通過對《理想國》和《斐萊布》的討論,本文指出,“大與小”——作為一對相對性對立和矛盾——本質地不是任何形式或確定性。因此,“大與小”和僅僅“偶然地不是”某形式的質料迥異,也因而和《蒂邁歐》中的“接受者”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