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今天的周一談治學欄目,為大家精選了武漢大學哲學系鄧曉芒教授的訪談《“成人”的哲學》一文,從生活與哲學、中西文化比較、反思與批判、否定性哲學這四個方面,帶你走進鄧曉芒教授獨特的哲學體驗,希望在這字裏行間,能觸發你的哲學激情和沉沉思考🦫。
下文節選自“學術月刊”公眾號文章《“成人”的哲學——鄧曉芒教授訪談》,有刪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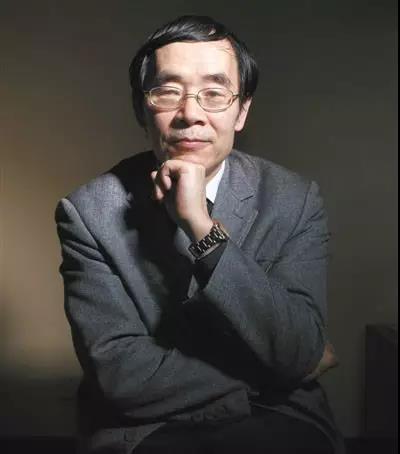
Q│欣文《學術月刊》編審
A│鄧曉芒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思辨的張力——黑格爾辯證法新探》,《冥河的擺渡者——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等。譯著有康德的《實用人類學》,《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三大批判”以及胡塞爾的《經驗與判斷》(合譯)等🥫。
1、生活帶給我哲學的興趣
Q:鄧教授🤞🏻,我曾從旁了解到您的經歷📅,感到十分驚異。可以說您完全是通過自學而取得進入學術界的學力的。在十多年的知青下放和從事體力勞動的過程中,您以初中畢業的學歷為自己打下了厚實的哲學基礎👫🏻,而且涉及如此廣泛的文化知識領域,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能否談談您的自學經歷🫷🏻?
A:其實,那時我自學西方哲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是一種興趣而已。這種興趣不是天生的👩🏼🍳,只能是生活帶給我的。我就是想要搞清一些社會的問題🍢、歷史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我自己的人生的問題𓀛💇🏽♀️。所以我對哲學的理解是很廣泛的👩🏽⚖️,它與整個人生都密切相關,而且不僅僅是我自己的人生,也包括別人的人生,甚至包括文學作品中的人生,全人類曾有過的和可能有的人生5️⃣🧙🏿♂️。我想搞清別人的活法,各種各樣不同的活法,以便為自己的活法提供參考🕺🏿。所以哲學就是理解人,理解自己。在這方面,我覺得外國哲學展示了人生的各種不同的可能性,所以盡管一開始我什麽書都找來看,但後來慢慢就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閱讀外國哲學著作中去了👐🏽。但顯然,外國哲學對於我來說並不是一種“專業”,而是一種視野。
2🧜🏼♂️🥊、中西文化的比較與批判
Q🧙🏼♀️:您的工作本身就是中西結合的一個生動實例,即援用西方哲學思想的方法和觀點來分析中國的國情⚙️。您如何理解中西文化在當代的關系?
A:作為一個以研究西學為主的中國學者🚅,我的研究幾乎一開始就與中西比較結下了不解之緣⛹🏿♀️。當然,這種緣分最初還是朦朧的。最初意識到中西文化比較的不可回避性,是在1987年撰寫《靈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1995年出版)的時候。那時的初衷是想表達自己對人生的各種哲學體驗,但說著說著就發現💆🏽♂️,在任何一個題目上都會找到中西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為了說明這些境界🧑✈️,我不得不回過頭去讀了大量中西哲學和文學的文獻資料,越來越浸潤於中西體驗中那些看似細微實則意義重大的差異之中,結果最終寫成了一本主要是討論中西文化心理比較的書👭🏼。到了1992年寫《人之鏡——中西文學形象的人格結構》(1996年出版)一書時,我的中西文化比較的意向已經很明確了。該書選取了中西文學史上一批最著名、最膾炙人口的文學經典名著中的主要文學形象,對他們的深層文化心理作了系統的比較。我在書中並不想對中西文化單純作一種全面持平的優劣評判🧑🏽⚖️,而只想表達我對當代中國人的生存狀況的一種批判性的體驗,並通過這種批判而突顯出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否則的話,中西文化比較就成了一種純粹知識性的羅列🎺,而無法幫助我們走出今天所面臨的文化困境,更不可能促使我們突破自己的文化局限而創造出一種新型人格。
我認為🧑🏻🤝🧑🏻,當今時代,學術研究的一個更重要的動機應當是批判。自從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我對中西文化在各種不同領域和精神層次上的差異性作了很多批判性的比較,甚至為此專門開設了一門“中西文化心理比較”的選修課🥋,至今已上過八輪👂🏿。由講課稿中抽出的單篇文章已陸續發表📌,內容涉及中西語言觀♿🔘、中西辯證法🚗、中西人格結構、中西言說方式、中西法製思想🚵♂️⏫、中西建築文化、中西倫理與善、中西人生哲學♋️、中西本體論、中西懷疑論等等的“差異”👎🏼。之所以要尋求差異,正表明一種拉開距離進行批判的姿態,以此來反觀和批判中國傳統的狹隘眼光,生發出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以沖破傳統固有的局限性🧑🏼🏫,塑造一種新型的獨立而堅實的中國人格。
3🫱🏻、批判與反思🛌🏽:對思想的思想
Q:說到“批判”,最近您和楊祖陶先生從德文翻譯的康德的“三大批判”出版了,這是我國百年來引進西方文化的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成果💷。您對這件事有什麽感想?
A:我所進行的文化批判與康德的“批判”的確有內在的一致之處。我多年來一直都很註重對西方經典哲學文本的翻譯🚣♀️,如對康德的翻譯,其目的主要不是想成為一名康德研究專家,而是要通過忠實的原版翻譯👌,使中國人真正能夠讀懂康德哲學,將西方這一經典的理性思維形態“原汁原味地”把握住。
當然,要將一種異民族的文化思想“原汁原味地”介紹到中國來👼🏽,談何容易。有人甚至提出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現代解釋學已經證明,沒有任何介紹是不帶先入之見的👨🦽。但其實這種觀點本身也是一種悖論㊙️。當你說出“翻譯是不可能的”時🧑🏽🚒,你當然已經知道為什麽是不可能的💁♀️,因而已經知道所要翻譯的對象的意思了,因為如果你連這對象的意思都不知道♘,你怎麽知道這個意思不可翻譯呢?而既然你已經知道了對象的意思,不就已經在你心中實現了翻譯嗎?於是問題就只在於如何把你已經知道的那個意思表達出來,這就只是一個技術性問題了。所以嚴格地說🧘🏽♀️,我們只能承認絕對準確的翻譯是人們不可能實現的一個理想🧑🏻🎤,但這個理想畢竟是可以接近的😿💑。我所說的“原版”或“原汁原味”當然也只是相對而言的,是指我們在翻譯和研究西方哲學文本時要盡可能地客觀和忠實,盡量排除我們由中國傳統文化和心理習慣所帶來的對原意的扭曲和幹擾👮。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通過翻譯,盡可能多地從西方哲學文獻中獲取對我們有借鑒作用的新東西。所以與國內某些翻譯家不同,我們在翻譯中盡量避免采用可能引起人們聯想到中國人所熟悉的事物的譯名、成語和字眼,哪怕因此使譯文成了淡而無味的大白話,卻著眼於意思的直白和表達的樸素流暢。在譯康德的著作時,我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嚴格遵從康德原來的句式,不惜用長得不可思議的句子,把康德那些重重套迭的從句整合進一句話裏面去,在康德沒有打上一個句號的地方決不幫他劃一個句號。這樣做的目的🕉,也正是要避免因將完整的句子斷開而導致的信息失落𓀙,並通過保持康德原文那冗長繁瑣的風格,讓中國人習慣於短句子的頭腦也習慣一下德國人強韌的理性✅。事實證明,只要譯者牢牢把握住句子中的邏輯線索👷♂️,充分吃透康德所想要表達的意思𓀔,再長的句子也能被中國讀者所接受,這就起到了訓練和改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的作用。
除了翻譯以外🎹,梳理“原版的”西方哲學還需要對西方哲學史進行全面系統的把握。翻譯畢竟只是一種基礎,在翻譯的基礎上進行研究才是實質性的工作。在這方面,國內的西方哲學研究有兩個重要的薄弱環節。一個是在研究西方哲學家的思想時客觀性不夠🫲🏻,總是擺脫不了中國文化視野所帶來的一系列誤會和曲解,使西方哲學家的思想往往成了中國人已有思想的註腳,而失去了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另一個是由於現在哲學研究在中國越來越成為一種“專業”🧏🏻🫑,所以由專業分工所造成的狹隘性已經嚴重束縛了人們的眼界和頭腦,以至於許多研究者一輩子就是抱住一個哲學家不放,靠他吃飯🧝🏻♂️,其他一概不知👨🏻🎤。這就使西方哲學研究成了“盲人摸象”式的。只有對西方思想的整個傳統有整體的了解🧖🏿,才不至於抓住一個人就做文章𓀕,以偏概全,這樣你才能有資格說中西思想的比較和融通。融通不是為了把西方思想納入到中國人習慣的思維方式中進行削足適履的“改造”。當然“六經註我”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只能是走向“我註六經”的道路上的路標。這就要求對待文本的嚴肅認真的態度🏑,要求有耐心🧞♀️,把人家的書逐字逐句讀懂🫘,而不要急於一下子就說人家的某某學說就類似於我們古人的某某觀點🤲🍻,甚至說我們古人比他們說得更早,更精彩。
但不管是翻譯也好,研究也好,對於我來說都是進行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的手段,因而也是一種“成人”或“立人”的手段。在這裏🧀,“批判”不只是為了追求民族的自強,而是類似於康德意義上的“純粹理性批判”,即每一個有理性者都應當達到的反思的思維層次。西方知識分子之所以要把批判當作自己的天職,是立足於有理性的人的人性或人的本質之上的。在他們看來,知識分子是思想者,正如自我意識就是對自我的不斷超越一樣,真正的思想就在於不斷地反思🫳🏿,即“對思想的思想”🧖🏿♂️。思想不是什麽現成的東西,而是一種批判的生命活動,自否定的活動,它的建設性、積極意義是在超越的層面上表現出來的,是它所必然帶來的後果👩💼,但它本身的本質是否定性的,並正因此而是無條件的、自發的🫳、能動的⛪️🕴🏼。批判就是一個理性存在者的自我實現,是建立人的理性的必由之路。這樣的批判將顯示它的積極意義,就是確立一種新型的人格👩🏻🔧、一種新型的思維方式,就是建立一種獨創性的哲學🖇。
4、自否定哲學:一種“獨創性的哲學”
Q:很想知道您所說的“獨創性的哲學”是什麽🔳。
A:真正的獨創性哲學不是某個天才頭腦中偶然的一閃念,而是時代精神的體現🤏。當今時代在向我們發出呼喚🈶💆🏼♀️,要求當代知識分子把握時代的脈搏,為這個天翻地覆的時代提供一種哲學上的解釋,提供一種適應時代條件的新的人生哲學和倫理生活規範🧩。否則的話💷,所謂“市場經濟”就會等於物欲橫流。不過🎷,在這方面單純進行一種道德上的譴責是無濟於事的🫰。如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內開展得轟轟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討論”最後只能是無疾而終,就因為這場討論一開始就是一場道德運動𓀏,它把社會的墮落歸咎於某些人🏂🏿、主要是知識分子經不起物質利益的誘惑,不能堅守人文理想和道德表率🧑🦯,放棄了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良心的代言人的使命👩🏼。對此🧑🏿🌾,我提出了一種“新批判主義”的觀點。我認為🐶,在標舉一種人文精神或道德理想要人們去堅守或弘揚之前😟,必須對我們以往所認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理想作一種“自否定”式的超越。這不是為了自己在道德上“成聖”,而是為了積極投入當前的現實生活變化🤹🏿;不是用一種自命清高的道德來與“墮落”了的現實相抗衡,而是從現實的變化中尋求建立新型道德關系的契機💃🏼。這樣一種新批判是每個個人在現實生活的啟發下自覺地努力尋找自我🪂、深化自我。由於它在自己個人內心深入到某種“集體無意識”的層面,它實際上又具有全民族自我反省的意義。它繼承了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並將它提升到“人性批判”的更高層面🐇。
這種“新批判”的哲學根基👩👩👧,就是我在1997年提出的“自否定哲學”。我認為,“自否定”是人性之根🛗,因而也是萬物之根👩🏿🦰,因為人性就是“完成了的”世界萬物,自然向人生成🧎🏻。自否定不同於自肯定♘,如中國傳統所謂“誠”🛝;也不同於“他否定”,如道德上的他律。這是自己與自己拉開距離,把現成的自己看作只是一個有待於完成❗️,甚至有待於創造出來的潛在的存在者,即看作這個存在者的有待於否定和重塑的質料🧩。沒有這種否定和重塑,這個現成的自己就什麽都不是🕧,或者說它還不是“自”✡︎。“自”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即它一方面意味著“直接性”、“明證性”😼,另一方面意味著“間接性”、“反身性”。直接性表明它是由感性“親自”實現出來的感性活動,間接性表明它同時又是一種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活動,帶有自我意識的自覺性♈️。因此,自否定是一種感性的創造性力量,在這種創造中⏫,由於否定的活動是自己對自己作出的🐣🤲🏻,因而就既改變了自己,又保持了自己的連續性。自否定就是自生自造,無中生有,從潛在可能到現實,“太初有為”。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道家的核心概念是“自然”概念,但道家哲學把自然理解為“無為”即非人為,看不到人的意誌行為其實是更高層次的自然和本性💇🏿♂️。西方哲學則在“自然”概念中分離出一個“創造自然的自然”和一個“被自然所創造的自然”,前者比後者更高,是後者的否定,因為它用“人為”否定了“自然”。但它也是同一個自然的“自否定”,因為“人為”、“創造”也是自然🥤,而且更加是自然,所以它是自然的“本質”、真正的自然。道禪的取消人為、放棄意誌、破除執著,看似回復到自然而“返璞歸真”,其實反倒是最不自然的⛹🏻♂️🧘🏻♀️。所以我主張吸收西方哲學的這一人為精神🤾🏿,在道家的“自然”概念中劃分出兩個層次😷,即“無為”層次和“有為”層次,使自然完成它的自否定,由此成就一種適應當代發展需要的哲學🍢。這種自否定哲學主要體現為每個人以自己的靈魂結構為標本,對自己心中所暗藏的傳統文化基因作批判的反思🍢,但它的意義並不單純是消極的,而將帶來一種進取的🛩、獨立不倚的人格形態。因為“自否定”本身意味著一種邏輯上的人格同一性和普遍性,它是對每個人的個性、創造力和自由意誌的承認🟧,而且是連續一貫的承認。從此以後🔽,只有建立在自由意誌之上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才是值得提倡的,更重要的是👷♂️,才是當代中國人自發地願意接受的。
由這種自否定哲學來看當代中國人文精神👥,我們就會意識到,中國文化正處在一個“自否定”的轉型時期🐬。不是誰要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而是這個傳統文化現在已經自己否定著自己,這正是這個幾千年的古老文明重新煥發生機的難得機會。實際上,自從一個世紀前皇權解體之後,歷史就已經給中國人提供了這種機會🟡,但由於逝去的亡靈不斷復活並糾纏著中國人的頭腦🧙🏼♂️,中國人對自否定的必要性的意識始終處於動搖和模糊之中。直到改革開放以來,現實中發生的巨大變革迫使我們重新尋求我們的生存根據,我們才意識到必須在一片從未涉足的荒原上靠自己的創造精神去開拓民族文化的未來。一種對新型價值的呼喚🧘♀️,向從事精神生產的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了創造真正有價值的精神產品的任務。在今天,只有個性化的哲學才能吸引人們的註意力🧎🏻♀️➡️,才能對人們形成自己的個性起一種激發作用。這種哲學不需要強加於人🫰🏽📵,它不是一種說教🧚🏻,而是希望任何一個人心悅誠服地理解它的原理,就像蘇格拉底所說的那樣🥒,真正的美德只不過是一種知識而已🦐。
當然,“自否定哲學”還只是提出了一個綱要,它還有待於完成。可以說🧍🏻,迄今為止我的一切學術研究和思考都是為了建立這樣一種哲學,因為它是我自己的哲學。我參考的是中國和西方哲學家們的思想,但我的立足點既不是中國傳統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我在幾十年現實生活中的個人生存體驗,是我對這個時代精神生活大趨勢的感悟。我為這個時代而振奮、呐喊,因為它是我的時代😋,它必須、也必將造就它獨特的成就☎️。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們不要辜負了我們的時代。
以“批判”為動機做學術
用“拉開距離”的方式沖破局限
塑造獨立堅實的中國人格
體現時代精神的獨創哲學
“我們的生命只有一次🤟🏻🫗,
不要辜負了我們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