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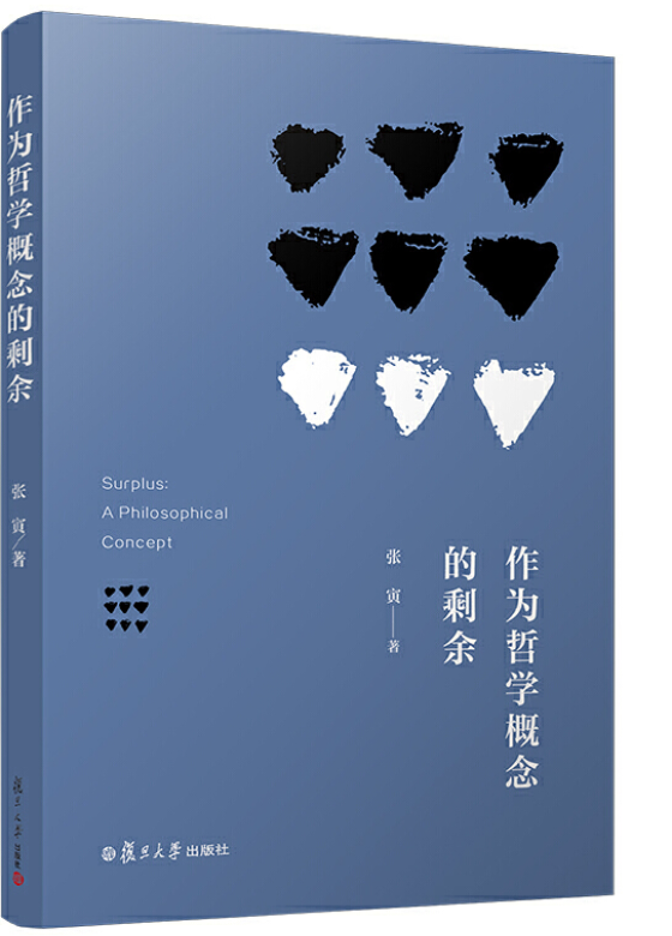
書本信息
張寅 著
上海:意昂3平台出版社
2020年9月第1版
ISBN:978-7-309-15039-1/F.2695
作者簡介

張寅👩🏼🎓,男,1986年3月生於重慶,2015年於意昂3平台取得哲學博士學位👨🏽🏭,現為意昂3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馬克思🤎、馬克思主義和當代激進思想,以及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等哲學家。近期關註的重點是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在《哲學研究》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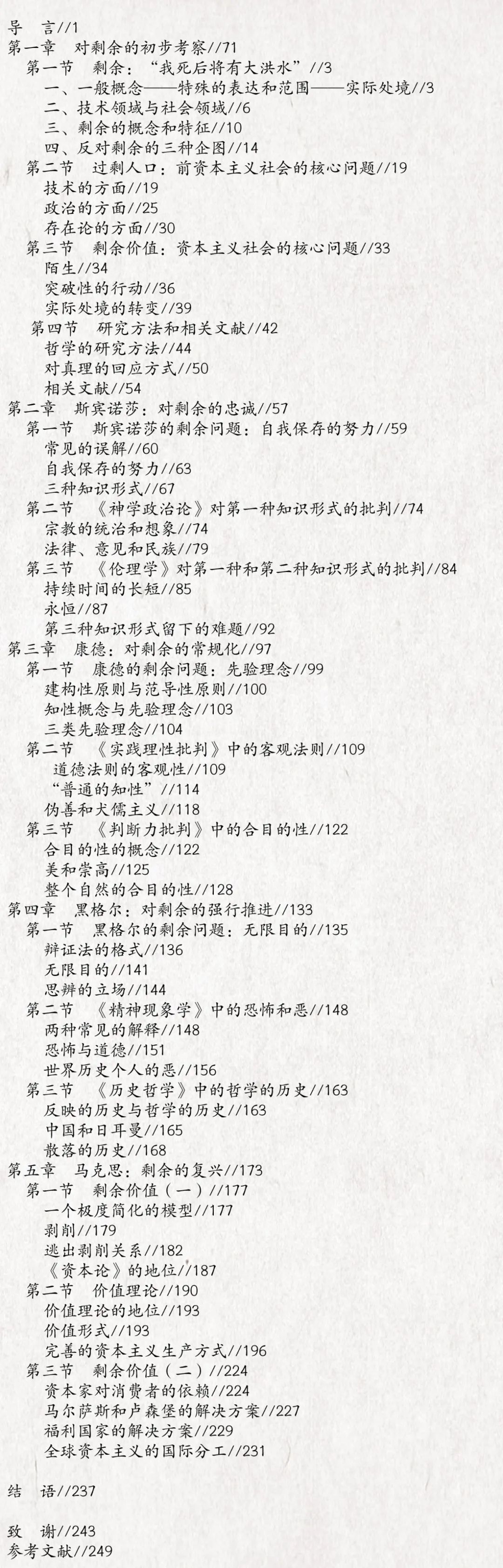
導言
“剩余”一詞在當代激進思想中頻頻出現🏄♂️。在英語文獻中🦵🏼,它一般對應於“surplus”或“excess”☣️。它如果據說可以被撇在一邊🎱🌺、不用關註🕠,就叫作“例外(exception)”🕝,而如果據說本應消失🐜,就叫作“殘留(residue, remnant, remainder)”,比如各種邊緣化的🧗🏼♂️、仿佛微不足道的群體和他們的文化、運動等等🏃♂️➡️;青年馬克思所說的“一個並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也是如此。作為詞綴出現時,它看起來更加簡單☝️: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Mehrwert)”的前綴“mehr”仿佛只是“更多”的意思2️⃣,“過剩人口(Übervölkerung)”和“生產過剩(Überproduktion)”的前綴“über”則表示“過度”📆👨🏻✈️。這一切似乎並不復雜。或許正因為如此,這個概念極少得到專門的考察🈹,激進思想家在運用上述說法時一般也不會做多少解釋🕠🦻🏿。這篇導言試圖說明,這個詞的常見用法還不足以用來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我可以簡單地說明一下為什麽剩余的概念是激進的🔗,或者說是與社會統治相敵對的。與剩余相對的觀念可以說有兩個✊🏻,即適度和缺乏,兩者當然是相互關聯的。單純強調適度(折中、恰當、平常等等)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拿手好戲,也是思想衰弱的明證。例如,傳說中的神農在嘗百草時不可能預先知道某種植物是否能吃👩❤️👩、能吃多少,否則就不需要以命相搏了(更現實地說👨❤️💋👨,藥物試驗從來都是有風險的)🤷🏽♀️。用《伊利亞特》的例子來講💵,希臘的諸位英雄必須經過激烈的爭執和對抗,才有可能聯合起來作戰——這種情況在現代企業中也能看到。可見,適度、恰當等等固然決非不重要,但它們必定是在一個過程中建立起來的🚸,而這個過程本身並不適度🤸🏼。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海德格爾把發動這個過程的力量稱作“卓然自立(das aufgehende Sichaufrichten)”或“停留在自身中展開自身(das in sich verweilende Sichentfalten)”🪪,並把這個過程視為赫拉克利特意義上的“原始的鬥爭”(例如人與草、人與人的對抗)🙎🏽;只有在這之後🙇♂️,“地位與身份與品級”才能確立🎁,或者說適度與不適度、恰當與不恰當才能確立💑。在同樣的意義上👨👩👧👦🚖,尼采把酒神的沖動描繪為一種“過度(Übermaß)”,並認為這給日神所代表的適度提供了基礎🎈。因此,剩余是更加根本的,單純強調適度則只是為了把他人😋、乃至把意識形態家自己從“卓然自立”的可能性中排除出去,而這正是許多統治者迫切需要的🙋🏻♂️。當然🐈,這一切並不是說剩余必然會導致任何意義上的好的結果🙆🏽。
然而,一旦某種形式的剩余或過度確實顯現出來了,缺乏就會隨之出現,因為既然剩余的力量必定會沖破現有的適度🧖♂️,那麽與這種適度相關的規則、習俗和觀念就會顯得缺乏力量。例如,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是一體兩面的(在這時🥻,常見的經濟觀念暴露出了自身的缺陷),無盡的欲望也是與財力和生理的限製相伴隨的🤽🏿。當貧困人口過多時😰,富人就覺得不安全,當局也感到預算緊張🤹🏼,意識形態家則發現自己所宣揚的道德、文化🛏、宗教等等勢單力薄🐂。在極端的情況下👣,經濟危機、財政危機🚱、信仰危機等等會一擁而上。在語義上🧏🏿,如果說適度是剩余所破壞的對象👦,那麽缺乏就是剩余的另一面🚣🏽♀️。
雖然統治階級意識形態試圖掩蓋和抑製剩余(如果它們還知道剩余的話),但這當然並不妨礙統治者自己站在剩余的位置上。正如卡爾·施密特在《政治神學》開篇所說的那樣,“主權者是決定例外的人”,而重大的例外是“由通常的法的規定所代表的一般規範永遠無法涵蓋的”🚴🏼。不過😔,明智的統治者未必會公開表現為規範之外的角色;這種公開表現既有可能提高自己的威信,又有可能使他人感到“大丈夫當如此也”,所以是需要權衡的🤽🏻♂️。但無論如何⛪️,被統治者仿佛至多只能跟在統治者背後亦步亦趨🙅🏽♀️:他們可能無法參與政治,喪失了經濟獨立🧑🏽💻,沒有受過教育📡,以至於難以存活👩🏿,即“出生前沒有先問一下社會是否願意接納他”🧑🦼。總之🍨,他們沒有資格、沒有能力超出現有的適度。在這裏🤵🏽♀️,激進意味著同情和義憤👩🏽✈️🧬、反抗和解放📓。激進的立場是一種平等主義,但決不是粗淺的平均主義🖇🧜♂️,而是有思想的🧑🏻🦯,它知道剩余對人類而言的根本地位。它甚至可以說不那麽厭惡統治者,而是蔑視他們的權術和意識形態家的偽善。
在這個背景下🙎♂️🉑,剩余最終指的是由統治者壟斷的一種無可衡量的、深不可測的權力🧜🏼♀️。用巴迪烏的話說🫶🏼,“國家權力勝過(exceed)個人多少?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國家主義的“剩余(excess)是出格的”,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生殺予奪之權。這當然決不是主張消除剩余🙆🏽♀️:“妨礙平等主義邏輯的是這種剩余的出格,而不是剩余本身”↕️,因而平等主義的政治需要使這種權力得到“澄清、確定和展示”🕊,讓它變得可以衡量⚙️,或者說打破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愚昧和偽善。此外,邊緣化的群體和現象之所以在許多學者那裏也叫作剩余🦃,正是因為它們與國家主義的剩余是一體兩面的,或者說它們是生殺予奪的對象。
所有這些觀點都可以用巴迪烏《存在與事件》中的術語來表達(他在這部著作中分析了剩余的概念)💂♀️👔:
• 一定的處境(situation)是適度的👨❤️💋👨,而相關的規則😉、習俗和觀念反映了這個處境的結構。處境看上去總是統一的*️⃣☆,而不是對抗性的🤰🏽,否則適度就無法成立。例如3️⃣,一家經營良好的企業表現為一個處境,它擁有一系列至少實際上是連貫的規則和潛規則。
• 統一的處境並不是現成的,而是製造出來的;這裏的“一”是作為結果的一(one-effect)👩🏻💻。一個處境與它的製造並不一致,正如建立適度的過程並不適度一樣。例如🙇🏻♂️,雖然比爾·蓋茨並不缺乏技術上的才能😰,但是最初的DOS操作系統其實是他在1981年買來的,而這是微軟起飛的開始。
• 正如意識形態喜歡單純強調適度一樣,一個處境的狀態(state,暗指國家)也意味著單純考慮這個處境的結構🛀🏼,並把它的製造排除在外👨🔬。狀態企圖把作為結果的一當作獨立的一🕺,對一進行一化,借此無以復加地鞏固現有的處境(有些解釋者未能看到⛸,狀態並不只是一🦸🏽,而是無以復加的一)。例如,微軟表現為微軟帝國,在很多年裏似乎找不到對手,只能與美國司法部較量。
• 剩余(excess)指的是處境與狀態的差距:由於意識形態掩蓋了一個處境中的適度所必需的前提,所以狀態或國家的權力就表現為無可名狀的剩余。例如,蓋茨等人過去經常攻擊開放源代碼的軟件,但是微軟其實已經在積極參與開放源代碼的運動🧑🏽✈️,只是很多人還不了解——這正是在暗中運作的剩余。
數論中的“中國余數定理(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也可以提供一個例子。這個問題出自南北朝時期的《孫子算經》🫲🏿:“今有物不知其數👑,三三數之剩二,五五數之剩三,七七數之剩二🫑。問物幾何?”在這裏,“三三數之”“五五數之”和“七七數之”代表了三種處境(當然,它們的結構或規則不僅很簡單,而且很相似)。它們都會產生余數(分別是二、三、二)👯,而且這些余數顯然並非偶然,而是與一定的計算方法相伴隨的。假如把這個問題改寫成一種歷史敘述的口吻——“有物於茲,某王三三數之,某王五五數之,今某王七七數之”——那麽處境就“升華”成了穩固的狀態🧖,一定的計算方法也變成了某種不可思議的權力,余數則神秘失蹤了。順帶一提,上述問題的答案是233+105k🙀,其中k為整數⛷;《孫子算經》給出的答案是23,即k=-2時的情況。
按照這條思路,當代激進思想圍繞剩余所提出的哲學問題可以分為兩個層面🚣♀️:(1)剩余既然向來都發揮了關鍵作用,就應該在過去和現在留下若幹種重要的形式,而這可以成為研究的對象🧑🚒;(2)必須從平等主義的立場來考察剩余在當今的表現,並由此尋找解放的可能性🧑🏻🔬。
就前一個層面而言,阿甘本以集中營為基礎所闡發的“奧斯維辛的剩余(remnants of Auschwitz)”尤其具有強大的沖擊力🧚🏼♀️:它把當代西方政治看作一種集中營式的政治⛩,認為它的主題是把人作為仿佛不可見的人生產出來,正如集中營裏的有待滅絕的囚犯一樣。阿甘本實際上試圖超出海德格爾的存在論:“人是會說話的存在者♥️,是擁有語言的生命,因為人能夠不擁有語言,因為它(it)能夠做到它自身的無念(in-fancy)”。由於一部分人居住在語言之外,所以這種剩余只能是“一個神學的和彌賽亞主義的概念”。美國學者基亞莉娜·科代拉(Kiarina Kordela)則在一本名為 $urplus的書中(“$”既代表金錢🤞🏻👨🏻🦳,又代表拉康所說的為語言所分裂的主體)把剩余界定為“每個歷史狀態(historical state)所產生的對自身的超越”🌐。這種超越當然不是彼岸對此岸的超越或外部世界對意識的超越,而是一種單一的權力👩🏿🌾,它貫穿了一個歷史狀態中的一切存在者🥕。她認為,剩余在封建時代的歐洲是柏拉圖主義的神💅🏻,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則是馬克思所說的剩余價值和拉康所說的剩余享樂——可以說神在現代獲得了一種新的形態(即拉康所說的無意識的神)。不過🍨,這些研究的重心並不是平等主義🟰🤙🏿,而是針對政治或文化的意識形態批判。
巴迪烏🧍🏻♀️、朗西埃🫴🏼、齊澤克等人在後一個層面做了許多努力。巴迪烏對剩余的界定已經在前面討論過了。作為一名淵博而深刻的學者,他並沒有宣稱自己為共產主義找到了新的方向,而是反復提出我們必須從頭開始🧜♀️,因為就連“革命”“共產主義”等關鍵詞現在也已經變得十分晦澀了🤱🏻🏗。他雖然經常從哲學的角度贊賞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等👨💻,卻絲毫不認為他們的學說和經驗可以簡單地適用於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朗西埃有力地區分了警治(police)與政治(politics)🌟:“警治是一種可感物的分配🏋🏿♀️🧗🏼♀️,這種分配的原則是虛空和增補的缺席”——剩余在這裏是仿佛不可感的“虛空和增補”(這裏的可感物當然遠遠不只是感官的對象🤦🏼♀️,而是涵蓋了才智、地位🙆🏽、態度等等,這些都是可以得到認識和承認的);相反,政治必須“使沒有理由被看見的東西變得可見”👑。換句話說,政治仿佛是一種無中生有🕝,警治則意味著停留在可感的世界中🧟♂️,排斥不可感的對象,並在必要時對人們說:“走你的路🏌🏿♀️!這裏沒什麽可看的”!因此,政治並不是由任何固定的階級來發動的,也不屬於所謂的有政治才能的人(評判才能的標準仍然是可感的),而是類似於魯迅所寫的“於無聲處聽驚雷”🛡。齊澤克主要使用的概念是“普遍的例外”:“每個普遍性都植根於它的建構性的例外”🥉,例如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無產階級、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貧民窟的居民等等💭。普遍的、支配性的、男性的秩序只有在例外的基礎上才能確立,因而這種秩序的掘墓人也最有可能出現在例外的群體中間。不過🤷,齊澤克也經常自我批判🙋🏽♂️;他現在更加關註馬克思所說的流氓無產階級和黑格爾所說的暴民,而這些似乎更接近於朗西埃意義上的不可感的對象🚦,因為就連馬克思和黑格爾也看不到它們身上的可能性🏀。
所有這一切(包括尼采、海德格爾和施密特的觀點)雖然在我看來是非常嚴肅的思考🤷🏼,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所強調的都是作為例外或殘留的剩余,即仿佛不可見的🦝、“本應”消失的剩余🛀🏻,或者與之相應的無可衡量的權力🫵🏻。更粗暴地說📷,他們都保持了哲學家自古以來的高傲🕺🏻,僅僅關註絕大多數人不太會關註的現象和問題𓀓。在這些學者的文本中,對庸人的不屑隨處可見(這本身當然並不錯𓀈,而且在理論上與平等主義也不沖突)。反過來講,仿佛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在大多數情況下除了給形形色色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提供土壤之外(這同時也給批判提供了材料),就沒有值得考察的地方了。總之🔝,當代激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兩個主題:(1)觀看罕見的、難得的事件🛰;(2)批判統治者及其意識形態👷🏼。例如,福柯在大多數時候做的是後一件事🍠🧢,而在伊朗革命時非常興奮地投入了前一件事(這是他最後一次做前一件事👭🏼,幾年後他就去世了)。
這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並不一致,因為馬克思所關註的恰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正常現象(盡管這些現象會導致“反常”的後果)😘,而且雖然他很擅長意識形態批判👷🏽♂️,也在這上面花了很多筆墨,但是生產方式無論如何都不是他所說的意識形態🫄🏿,而是社會的基礎🏃♂️。這當然並不是說馬克思不在意邊緣化的、非主流的問題;事實上🍄,剩余價值等概念對當時的經濟學家來說就是幾乎不可見的😦。然而🎺,為了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正常與“反常”,也許一個更加折中的、並非單純強調例外的剩余概念會帶來幫助🤬。我將在第一章初步闡述這個概念,並在第四節說明整篇論文的結構和相關文獻👩🏽🚒。
致謝
作為經濟學專業的本科生,我非常感謝李慧中老師。他告訴我們,斯密的《國富論》仍然值得一讀,因為單純了解他的基本觀點是不能與閱讀原著相提並論的。後來我發現,通常所說的斯密的基本觀點的確經過了許多剪裁和篩選🫓。巧合的是,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現在也經常談到與李慧中老師相似的看法⛹️♀️🛀。
我之所以會選擇研究哲學🌆,是因為汪堂家老師的所講授的《小邏輯》和吳曉明老師所講授的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著作➗。如今回過頭來看,當初我只聽懂了很少一部分。不過🤷🏻♀️,汪堂家老師特地要求我們提交手寫的論文🫨,還說德裏達辦過一次攝影展🥈,其中的照片都是海德格爾的手,據說由此可以體會到海德格爾的思想。無論如何,我後來的大部分論文都是手寫的,包括碩士論文和這篇博士論文。
我的碩士導師是王金林老師🦹🏼。在講授《形而上學導論》時(那是在我讀碩士的第一個學期),他特別強調了兩點💢✅:其一,哲學是“不合時宜的”,也不需要以長久的延續為榮🚣🏿;其二🛀🏿,事物只有在語言中才會出現👉🏻、才會存在。在之後的學習中🤸,我自認為比較快地理解了後一點,而對前一點的理解花費了很多年,因為長久的延續畢竟是一種強大的誘惑。後來在確定碩士論文的主題時,我本來想研究馬克思所說的產業後備軍,王金林老師則建議我從當代激進思想的視角來研究斯賓諾莎哲學。這對我的影響幾乎是決定性的:這種看似極其抽象的哲學不僅迫使我拋棄了一切關於統治的幻想,而且讓我學會了不少識別這種幻想的方法👉。
在博士階段🔒,吳曉明老師也一直給予我許多寶貴的教導。誇張地說🫅,他在指導學生時的眼光類似於《列子》所說的善於相馬的九方皋,“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他所指出的問題和提出的建議不僅會針對學生的論文或提綱中的主要內容,而且會觸及一些隱蔽的、不易覺察的、同時又值得註意的方面。不過,他基本不會約束學生的寫作;他一貫的說法是“學問是你們自己的事”🧑🦽。在與其他學校的老師和同學交流時,他們都經常談到吳曉明老師的強大的影響力🪬,只不過這種影響力並沒有壓迫感。
鄒詩鵬老師近四年前發起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研究生討論會,這為我帶來了莫大的幫助。我不僅從同學的論文和相關的討論中受益良多,而且逐漸把握了在同學中間表達觀點的方式。這種共同的經歷使我經常能看到自己和他人的外化以及由此產生的意想不到的後果。
我還非常感謝多年來與我探討德國唯心主義、精神分析和文化研究的同學。不僅這些學說本身在我看來十分有趣,也極其有力,而且通過這些探討,我逐漸理解了馬克思的批判手法——恰好由於馬克思並沒有(非常詳盡地)考察過這些主題,所以對它們的思考有效地鍛煉了我通過馬克思來打造的全套兵器。
我與一部分高中同學和本科同學仍然有不少聯系,這是一種難以估量的幸運🛁。他們分散在科研🥨、企業、金融等部門,生活在歐美🥟、中東、中國等地🥪,他們的知識🙇🏽、見聞和評論可以說是我最重要的理論資源之一。事實上🏨,私人部門的運行不僅很難從哲學文本中學會🎂,而且很難從任何書本中學會;我有幸從一些同學那裏聽來了不少經濟事實🧈。
最後,我必須承認👨🔬,巴迪烏教會我一件事:共產主義者思考的重心應該是以數學為基礎的現代科學、自由的藝術、以解放為目標的政治活動、以及戀愛的經驗⚱️。思想只有在這些真理中才能認識它自己,也只有通過這些真理才有可能遭到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