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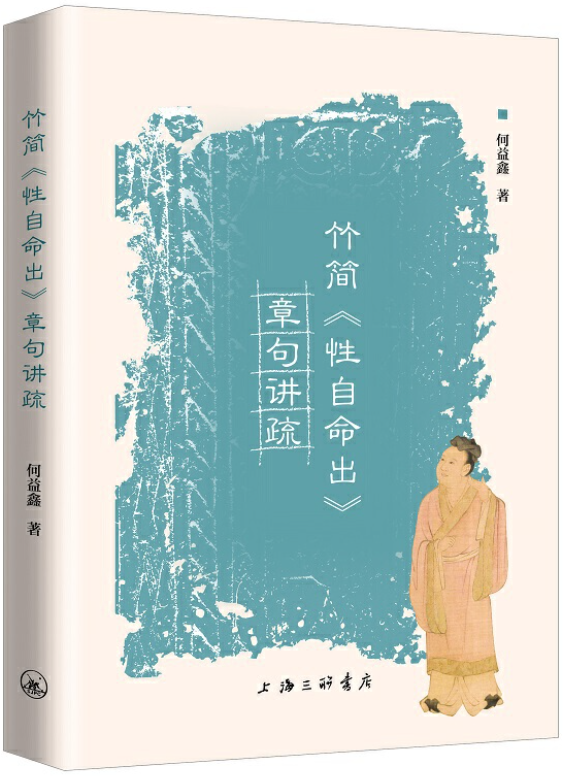
書本信息
作者:何益鑫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出版年月:2020年8月
ISBN:978-7-5426-7070-0/B.683
作者簡介

何益鑫,意昂3平台理學學士🎾、哲學博士🙋🏻♂️,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博士後🕎,現任教於意昂3☎️。主要研究方向為先秦儒學、《周易》卦爻辭🧎♂️➡️。著有《成之不已:孔子的成德之學》《竹簡〈性自命出〉章句講疏》等。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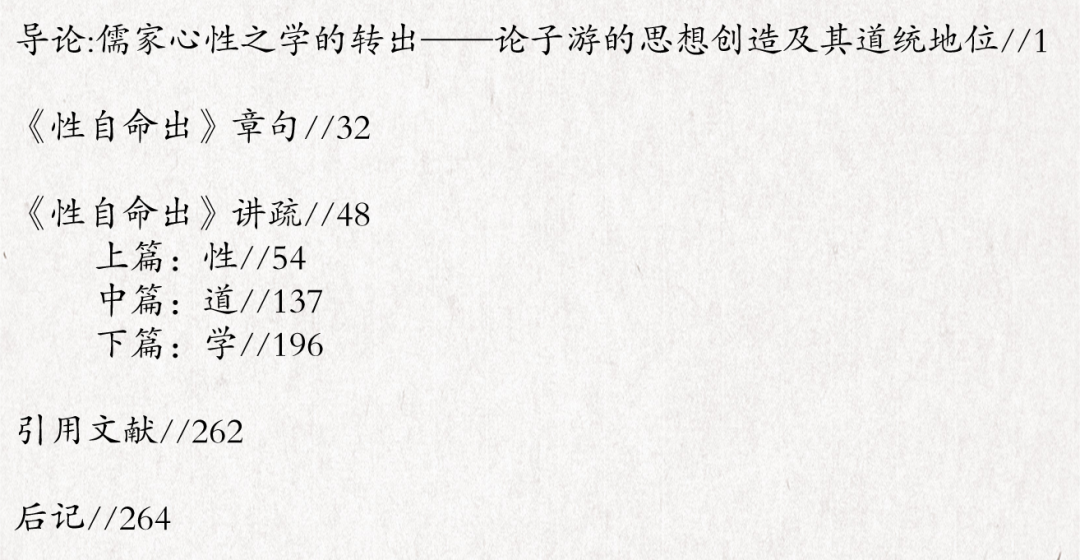
導論
儒家心性之學的轉出
——論子遊的思想創造及其道統地位
摘要:子遊是孔門後期弟子的代表人物,是儒家心性之學的肇端。從《論語》等記載看,子遊得力於禮樂💆🏽♂️,尤其對樂教有深入領會。他對“本”的重視,源於樂的造詣。他關切人的內心的生存活動與情感狀態🗡,將之視作為學工夫的出發點和落腳處🌂,並從人情表達之需要的角度重新理解禮樂製作的意義。由於對內心的意識現象和情感活動的長期關切和反思,在《性自命出》中,子遊展示出了一條以人性發生學為根底的,以天👩🏭、命、性、情、道🗯、義等為邏輯環節的新的思想道路🧕🏿。此道路,貫通天人、內外,融攝《詩》《書》禮樂,經由“心術”的工夫,歸於“生德於中”的宗旨。它在繼承孔子之學的德教本質的同時,為教化的必要性和方式作出了新的論證,也為後人討論人性、性情、心性等問題提供了思想框架❤️。它開啟了思孟心性論,其具體形態又有別於後者,可稱之為“性情-心術論”🧗♂️。如果說《論語》等所見的子遊重本的傾向,是子遊之學的早期發端;那麽🧑🏼,《性自命出》的“性情-心術論”🥨,則是其長期沉潛之後的展開形態。子遊由對“本”的關切與思考✢,轉出“性情-心術論”的思想道路,是儒家心性論轉向的關鍵人物。今日若重論道統👨🏻🍼,在孔子與子思之間,除了曾子之外,還應當有子遊的位置。
關鍵詞:子遊👩🚒,性自命出,重本,性情-心術論,道統
孔子以其典範性的生存,成為七十子後學乃至整個儒學的最高理想🧑🏽⚕️。他的思想和言說與其生命實踐融為一體😧,處於一種尚未剝離的完滿狀態之中。但這種狀態不是人人皆可契會的。於是,如何從孔子的學思典範中,引出一條可理解的思想進路,以便更好地理解孔子、闡明孔子,也為了更好地指導實踐,這是七十子後學的思想使命✊🏿。此間,子遊可以說是關鍵性的人物。他的偉大之處🤾🏻♀️,正在於其思想的創造✍🏻。他擅長文學🖖🏽,尤得力於樂教,故其學重本👨🏻🚀。他反身向內🎞,關切人的內心的生存活動與情感狀態,由此沉潛,轉出了一條“性情-心術論”的思想道路,成為了思孟心性之學的先導💸。
子遊,姓言,名偃,少孔子四十五歲🚀,與有子🏄、曾子♍️、子夏👰🏼♂️、子張相仿🧝🏿♂️。《論語》列“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共十位代表(《先進》)。前三科的代表,都是前期弟子;唯“文學”(禮樂文章之學)列子遊、子夏,是後期弟子的代表。前期弟子重實踐🏥,後期弟子重文學。但同是以文學著稱🙁,遊🫗、夏之間仍有重要的差別。要之☛,子夏註重傳經,《六經》的傳承,子夏居功至偉;子遊擅長思想,由禮樂文章的沉潛而開顯出思想的道路👉🏓。
關於子遊的傳世文獻,散見於《論語》、《禮記》、《孔子家語》等,不是很多。以往有的學者指出🧝🏽♂️,《禮記·禮運》為子遊所作🙋🏼♂️。但思想史的研究表明,《禮運》是戰國中期盛行的禪讓思潮的“一曲挽歌”,應出於子遊學派後期學者之手,而不會是子遊的作品。不過,郭店竹簡有一篇《性自命出》,各種證據表明,很可能是子遊的作品🔲。因此,我們對子遊思想的考察,主要依據兩種文獻🗡:一是傳世的先秦文獻,尤其是《論語》🧑🏿💻;一是郭店竹簡《性自命出》。
一、《論語》等所見子遊的重本之學
子遊🎹、子夏皆擅長於禮樂文章。不同的是,子遊有自身得力之處👩🏼🏫,故不滿足於此,而有進一步探尋文章之本的要求。於是,有了子遊𓀄、子夏的本末之辨🧕。
子遊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𓀔:“噫👰🏽♂️!言遊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論語·子張》)
朱子於此章頗為用力。在《集註》中🦀,他自己先解釋了一遍👩👧🌁,然後不憚其煩地四引程子之言。反復強調的是,灑掃、應對🖥、進退的下學與高且遠者的上達🦹🏽♂️🌁,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近者💮🧑🎓、小者與高者👩👩👦👦、遠者🐔,本末一貫,不可分為兩節。如程子說💑,“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朱子按雲🧛🏼♂️:“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顯然🤩,宋儒是站在了子夏的一邊,批評子遊對子夏的批評。
程朱的說法,在理學系統中不難理解。但這一立論與批評🙆🏼,能否切中此間的核心關切,則未必🛏。這裏牽涉到為學宗旨與根據等問題🙆🏻。
其一🌿🕍,宗旨問題。同是做一件事,存心與立意直接決定了它對人而言的可能的生存論效果。子遊的本意,未必是說門人不要灑掃、應對、進退,而是批評子夏教門人🧑🏻🤞🏻,根本不立、宗旨不明。故其門人小子之灑掃、應對◼️、進退,也只是灑掃、應對、進退9️⃣,而難以化為成己成人、自得受用的工夫階梯。從這個意義上說,子遊的批評是對的🪃。子夏為人細謹,從他的角度說😮,以灑掃、應對、進退為門人小子進學之始✤,也未可厚非🩹;但問題是🧋,在此之前,門人是否已有一個確切宗旨在?先有宗旨🈷️,則一切細謹的活動,皆可在此宗旨之下得以安頓,成為成德之學的內部環節。否則📑,縱使做的再好🧑🏻🦲🤴,不免深陷細末,於根本無益🤘🏿。
其二,與宗旨相關,還有工夫的落處。為學工夫要有明確的落處。每做一事,都想著把它做好,這也是一個落處🤽,但此落處是離散的、無盡的、逐物於外的🥑,與人的總體生存是不貼的。為學的真正落處,應當在具有總體意義的人的德行。《中庸》雲:“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人的至德,乃是道的凝聚之處👩🏽⚖️,亦即工夫的落腳處。此落處🌒,孔子則謂之“己”。身在孔門👩🏻🔬,無人不知孔子之學是“為己之學”👧🏼,只是對“己”的體認與理解不同。為己,不僅是一種發心(為了真己)⚪️,更是為學的方向和方法:時時從切己處出來,又時時回到自家身上。如此用功,則一切具體的為學活動⚂🦪,皆可匯入這個“己”,凝結為人的德行。否則,即便不斷為學,也沒有一個真實的“己”來承納這一切,活動的意義無處附著。唯有在德的統攝之下,為學的活動才能轉化為成德的資糧➔。這個方面,子夏是有所欠缺的。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論語·子張》)子夏眼中的“好學”😔,是每天學一點新的東西😶🌫️,同時不忘記已經學會的東西🤚🏼。其著眼點是量上的積累,面向的是一個知識的“己”,而不是德行的“己”。
其三↕️,對“己”、對“德”的理解,又決定了工夫進路的選擇。子夏致力於知識和能力的積累👅🍃,對“己”、對“德”👈🏽,以及它們所依托的人的內心活動👩🏻🦼,是缺乏深刻的理解的。但子遊不同🙎🏽♀️。從《性自命出》看👨🏼🚒,子遊對於人的德行與內心活動的關系🌴,有一種清醒的認識;對於各種要素(包括教化活動)之於人的德行的長成的意義,也有一種清晰的理解🐓。這些認識與理解📊👮🏿♀️,是子遊思想成熟時期的表達,但這方面的關切🧚🏻♂️,應該是一以貫之的🕝。這就決定了他對為學工夫的進路選擇。我們可以推測🐡,子遊教門人,也會包含灑掃、應對、進退等內容。只是與之相比🙆🏼,他更加註重人的內在性情的宣發、塑造和陶冶👩🏻🦼,換言之🐝,他可能更加重視樂教。
子遊與子夏的這種差異🍆,從孔子對二人問孝的不同回答中,也可以看出端倪。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論語·為政》)
子遊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為政》)
但凡學者問孝,孔子都是應機指點,而不是給出通行的解釋🎽。其原因可能有二:一♢,與孔子對德行的理解有關。他對德目的把握不是訴諸於確定的定義,而是在具體的活動中看出、指示出它🤱🏼🧖🏼♂️。二😛,諸弟子之所以問孝🫵🏿,不是孔子在課堂上不曾講到孝,而是出於個人特殊的實踐要求,孔子是順此情境給予了具體的指點🦸🏻♀️。子夏問孝✹,孔子說僅僅服勞奉養是不夠的⛎,還得註意由內而外的顏色表現。所謂“色難”🏈,即事親時的愉色和婉容,這是出於內在的愛意的。子夏細行嚴謹🧲,奉養有方,但內在的深愛並不充沛,故孔子告誡以此。子遊問孝👨🏻🦰,孔子告訴他不能只是奉養,還要滿懷敬意📉。看上去,這與對子夏的回答相似,都是要回歸內心。但仔細看是不同的。子夏的不足,是缺乏內在的深愛🪑。但子遊的不足🔁,不是缺乏深愛,而是深愛無節🧾,以至於缺了敬意。一出於深愛,可以發自內心地有好的照料、好的顏色,但未必能夠讓父母感到尊敬。而事親之事,須得愛敬兼盡👨🏼💻。故孔子告誡他🧘🏻🫨,除了好好奉養之外🛅,還要敬重他們。子夏流於表面的奉養,子遊任其內心深愛的表達,這與他們的思想品格是一致的。
子遊重“本”🧙,但他沒有說“本”具體指什麽;或許,它就是一個指向🚴🏽💁🏼♀️,指示一種與“末節”相反的方向。在“本末之辯”中,它指向為學的宗旨⬆️、工夫的落處,以及真正源發性的內心的生存活動。而在問孝的例子中🦤🎤,它指向了內心的深愛之情🤽🏽♀️。這個意義上的“本”🚵🏼♂️,與孔子對“禮之本”的理解是相近的🐊。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孔子對林放的問很是欣賞🏧,感嘆說“大哉問”!孔子的回答也表明,所謂“禮之本”指禮背後所表達的情意或情感。與之相似,子遊曰👨🏻🦽➡️:“喪致乎哀而止。”(《論語·子張》)喪禮只要致極居喪者的哀情即可。這是針對過於註重外在文飾,舍本逐末而言的,與孔子之意相承。喪禮,無論具體的儀程如何🕵🏿,最終是為了表達和抒發喪者的哀情⛹🏽♀️。子遊的話❔,是為了回歸到這個宗旨上,這就是“本”。
子遊對本的理解,也牽涉了對子張的評價。
子遊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論語·子張》)
曾子也有類似的評價🧑🏼💻。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子張》)朱子《集註》引範氏雲:“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的確,子張的為人,誌意高廣⚀,很有威儀🛬。據《論語》,他學幹祿🏮、問十世、問令尹子文、問陳文子🍶、問善人之道🍽、問明、問崇德辨惑、問政🤽🏿、問達🎅🏼🩱、問高宗諒陰、問行、問仁、問從政🪨,皆可謂著眼不凡,但多直接用力於為政8️⃣✡︎。孔子對此了然於心,故其答子張問仁,雲“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乃是就從政而為言,不是心底的工夫🌕。子張的格局雖大👾,但問題是較少用力於為己、為仁。然而,仁是個人的修為🙎🏼♂️,是內心的至德🙂↕️🔱,真正的仁道必由此而出。子張於此不足🍴🥜,故子遊、曾子乃有如是的評論。值得註意的是,作此評論的不是別人👊🏼,正是特別註重內在德行修養的子遊和曾子。其所得如此🏌🏻,故所見如此📉。
子遊對本、對內心的意識活動與情感狀態的洞察和關切,使他對於人的觀察具有一種通透的眼觀和敏銳的覺知🫵🏻。
子遊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論語·雍也》)
澹臺滅明為人低調。何以知之?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曾說🫧:“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這不僅僅是說澹臺滅明相貌不好,必也是因為他平日為人低調𓀕,故以孔子之智一時也瞧他不出。但子遊卻識別出了他👃🏿,依據了兩點:路不走小徑,沒事不到邑宰之室🧑🏽。若就事論事,這兩點本身也沒有什麽。關鍵是子遊從中看出了澹臺滅明的為人和用心💆🏻♀️,而表之以這兩個細節。這樣一種由外而內的考察方式,與孔子所說是一致的。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論語·為政》)看一個人做事的方式🗯,觀察他的動機,識別他的內心狀態,便能深入了解一個人。但如此的洞見💇🏼♀️,源於一顆敏銳的內心🕴🏻,不可著相。
子遊的重本,應與樂教有關。子遊擅長禮樂🛣🫸🏽,尤得力於樂教。他的好樂傾向🧑🏽💼,在早年便已顯露⭐️。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論語·陽貨》)
子遊為武城宰,孔子帶弟子前去考察。一進城,便聽到了弦歌之聲🤽🏽♂️。孔子微微一笑,跟弟子開了個玩笑,“割雞焉用牛刀♥︎?”意思是說💨,治理這麽個小地方,也用得著樂教?子遊便以夫子素日所言答之🚈。在此,有兩點值得註意:其一,何以孔子會說“割雞焉用牛刀”🤷🏿♂️?試想,若子遊只是在武城推行禮教🔰,孔子恐怕不會如此打趣ℹ️。因為禮在當時是任何為政活動必由的途徑,其時效性也強。但樂不同,時間長🐖、收效慢,對於一般的小地方的治理,似乎是非必要的選項。其二,在這種情況下,子遊還格外重視樂教,說明他對樂教本身的特別重視。這種重視⌚️,必出於自身的體認。樂教關乎人的內心活動,關乎性情的陶冶,“其入人也深”(《禮記·樂記》)。推行樂教🏄,可以由內而外達到民德的風化。它雖不是立竿見影的措施,卻是培本固原的方法。
子遊關切人的內心情感狀態🤬🙍♀️,但並不因此忽視其外在的實現方式⇒🤾🏽♀️。實際上,他試圖從人的內心情感之系列變化及外化的過程,來為禮樂之必要提供一種重構式的論證。
有子與子遊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遊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踴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遊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踴矣。品節斯🔦,斯之謂禮🖖。”(《禮記·檀弓下》)
有子與子遊看到一個小孩因為找不到父母而大聲號哭。有子見此有感🦑,說他獨獨不能理解喪禮中對於“三踴”(一踴三次跺腳,三踴九次)的規定,像小孩子那樣縱情表達就可以了,何必要有具體的限製?有子之說🐗,著眼於內在情感的抒發😚🦾,是對“本”的回歸,也頗符合子遊“喪致乎哀”的主張🫱🏼✥。對此,子遊卻說,“喪之踴”的規定是必要的。他指出🧹:有的禮可以節製人情⬜️🕧,有的禮可以激發人情,最終是為了使人情得到中道的表達。人情的發生與表現,有一個自然的醞釀和變化的過程🥗。順著這個自然的過程加以品節🪒,才謂之禮𓀍。恣意表現🌋、縱情宣發,那是野蠻人的方式👼🏻🤍。
可見,子遊沒有因為對禮之本💂🏻、對內在情感的強調,忽視外在禮製規定的意義。事實上,子遊已經深入了人情的內在運作方式,來為禮製規定的必要性作出了一個新的論證。這一點是孔子所不曾做過的,開啟了一個新的思考方向👨🏼🎤💽。如果說,孔子的“禮之本”🏆,是從個人實踐的角度,調動人的情感的參與,以追求禮的最好實現🧨;那麽,子遊則已經以人情為基礎,以其內在的發生及表達為前提👆🏽,轉而從製禮作樂的角度論證禮的產生和存在的必要性。其後🚵🏿♀️📤,子遊學派《禮運》說:“禮義也者……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公孫尼子《樂記》說:“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自此以後,人情明確成為了禮的製作的內在根據🤦🏿,也成為了禮教的落實之處;聖人緣人情以製禮,成了儒家關於禮的起源和本質的標準學說。這一思想,與子遊(或許還有其他同門)從人情角度論證禮樂的思路轉變有莫大的關聯🤛🏻。
子遊在禮樂之教中對“本”的追求和體貼🤼♀️,使他特為關註人的內心活動與情感變化。順此以往⚛️,他逐步發展出了一套系統的“性情-心術論”思想。此思想🧖♂️,又反過來為其禮樂思想建立了更為穩靠的基礎⭐️。從習於孔子的禮樂之教🚫,到以“性情-心術論”的展開,融攝孔子的禮樂之教與成德之學🧑🏭,可以說是子遊之學的必然結果🧑🏽🌾。
二👳🏻、《性自命出》與子遊的“性情-心術論”
郭店竹簡《性自命出》(上博竹簡《性情論》大同小異),討論了天、命、性👩🚀、情、道、心等心性之學的核心概念。其所出的墓葬年代🐣,下限是公元前三百年🙍🏽♂️👠,則其著作年代還要更早🦹🏼♀️。從現有的資料看,它很可能是儒家對這些問題的最早的主題化探討。故被視為孔子之後、孟子之前,儒家心性之學的早期形態的代表。
《性自命出》的作者,有人認為是子思🦸♀️👩🏫,有人認為是公孫尼子👩🏻🦰,有人認為是子遊。主張子思的學者,看到了《性自命出》與《中庸》前三句的“隱括”關系。如姜光輝先生認為🛗,“《中庸》一書反映了子思的成熟的思想,其起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三語隱括了《郭店楚墓竹簡》中《性自命出》的內容。”從思想史的角度說,兩個文本具有隱括的關系,並不能推出它們是同一作者的作品👨👦。更有可能,是時代之演進和思想之提純的結果,具有思想史上的前後承繼關系。古人著述不易,如果學者的思想有所演進,或對同一命題找到了更為簡約或合適的表達🤷🏿,應該會直接體現在最後定本之中。更為重要的是,《性自命出》“道始於情,情生於性”,“情”是連接“性”“道”的核心概念,具有獨立的意義,在後續的修學過程中也是關鍵;但在《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的論述中,“情”字隱入了“性”字之中,未獲獨立的意義,在後續的論述中也未出現。之所以如此,我認為,《性自命出》的作者,深得於禮樂之教尤其是樂教🗝,由樂教對“情”的體認和陶冶,深入人性與人心的作用原理👍,從而轉出“性-情-道”的主張和基於“情”的教化之道。但據現存的子思文獻來看,樂教並非子思的得力之處,或者說子思的思想並非源於樂教對情的蘊藉,故其思想越過了“情”這個環節,而強調道德意識之“誠”,這是子思思想的基本特征。所以說,《性自命出》與《中庸》雖然在大思路上相似🦶,但關鍵處的把握卻有重要的不同,不會是同一個人的作品。
主張公孫尼子的學者〽️,看到了《性自命出》與《樂記》的樂論思想,討論的議題、使用的概念上的相通之處。但細致的考察會發現,兩者無論是思想展開的程度👱🏻,還是篇章主旨的核心關切,都是不同的。李天虹曾指出三點💇,其一,《樂記》的樂論,較《性自命出》更為豐富、深刻、明確;其二😓,《樂記》“知樂,則幾於禮矣”🫃🏽,禮的地位高於樂🧝,而《性自命出》“樂,禮之深澤也”,頗有重樂的意味💃🏽;其三,《樂記》的政教色彩比較重🤽🏿♀️,而《性自命出》則更註重個人的修養。所以,從思想主旨或核心關切的差異看,我們更願意將《性自命出》與《樂記》視為不同作者的作品。不過,從概念🧑🏻⚕️、議題的相關性看,兩者確有一定的繼承關系。考慮到討論的深度©️、表述的成熟度,以及對禮樂關系的把握方式等等,《樂記》應是在《性自命出》基礎之上的進一步的發揮✋🏼。《漢書·藝文誌》註明公孫尼子為“七十子之弟子”,即孔子的再傳弟子🚴♂️。從思想的演進歷程看🧑🏿🔬,若《樂記》果為公孫尼子的作品,則它之前,或有另一個文獻是其思想的來源。這一作品,可能就是《性自命出》。其作者,則是孔子的直傳弟子。
我們認為,《性自命出》的作者更有可能是子遊。從思想上看👉🧛🏽,《性自命出》最得力的地方就在樂教,而孔子七十子尤其是後進弟子之中🚣🏽,子遊在樂教方面最為突出🙅🏻。從年代看,子遊是孔子弟子,子思🛌、公孫尼子是再傳弟子👩🎤。若《性自命出》出自子遊,便可以理解,它一方面影響了子思《中庸》“性-道-教”的思想格局,一方面也影響了公孫尼子《樂記》的思想🙍🏽♀️。故陳來先生的推測:“或許公孫尼子就是子遊的弟子”🫃🏼;“很可能,子遊、公孫尼子🦹♀️、子思就是一系”。我們認為是比較中肯的。大體而言🍇,子思與公孫尼子同得於子遊之學,而取舍不同。子遊之下🙎♂️,公孫尼子或是子遊的直傳,由樂教方面的得力,撐開性情論的探討和禮樂教化的主張🧜🏽♀️。至於子思,在受子遊思想的啟發之余,也受其他弟子尤其是曾子的影響。他雖接受了子遊性情論的進路,但其得力之處終究與子遊不同🧝♀️,故修養的核心與思想的形態亦與之相別。
正是由於子思與子遊的這一段思想的淵源,荀子在批評思孟“五行說”的時候說:
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遊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荀子·非十二子》)
荀子說👧🏻,子思(和孟子)的“五行說”,乃是根據往舊見聞而自造新說的結果,卻自稱是孔子之言🫃🏿,後人也以為是傳自於孔子和子遊🐆。可見💈,在後世子思之儒3️⃣、孟氏之儒的自我認知中,“五行說”與子遊有一定的淵源☣️👨💻。這個淵源🐈⬛,很可能就在子遊的性情論,即此篇《性自命出》🏄。
更直接的證據是,郭店本《性自命出》的一段話(上博本缺),與前引《禮記·檀弓下》子遊的話基本相同👜🤹🏻。
喜斯陶😌,陶斯奮,奮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喜之終也👩🏿🏭。慍斯憂,憂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踴。踴👧🏽,慍之終也🕵️。(《性自命出》)
兩者的差別在於,《性自命出》分別論述“喜”🧜🏽♀️、“慍”兩種情感的發展變化💉,以“舞”為前者之終,以“踴”為後者之終📏。而《檀弓下》沒有了“舞,喜之終也”和“踴,慍之終也”兩句,中間多了一句“舞斯慍”👀,由“舞”直接過渡到“慍”🚟。這顯然不合邏輯。前人對此已有察覺,以為衍文🌼。但這一疏誤,當不是《檀弓》原本的問題,可能是後世的流傳或漢人的整理導致的🐙。我們認為,兩處應該是同一段論述。至於它們的關系,或許並不是誰引用誰的問題🧑🏽🦰,更可能是一個思想的原始表達與成熟表達的關系#️⃣。可以推測,子遊先是在與有子的討論中闡明了此意👱🏿♂️。而後在著入《性自命出》的時候,在“陶”“詠”之間加入“奮”、“慍”“戚”之間加入“憂”,以足其意;又加兩個“終”字以示區隔,形成了《性自命出》的最終表述👵🏿。後來👨👨👦,《性自命出》失傳📚🧑🚒,《檀弓下》在流傳💪🏼♙、整理的過程中,或人誤在兩層隔斷之處增入“舞斯慍”,造成了文義的糾葛🙆。
此外還有一個證據,即“有為”的觀念。在《禮記·檀弓上》中,曾子告訴有子🧑🍼,孔子曾說“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認定🕕,這不是孔子的話📏;如果是🥨,那也是“夫子有為言之”。子遊確證了有子的判斷,並大為感嘆:“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與此同時,在《性自命出》中,我們看到了四個“有為”:“有為也者之謂故”⚄,“《詩》,有為為之也🦡;《書》📹,有為言之也🤦;禮樂🪞,有為舉之也”🧚🏼。作者以“有為”來解釋“故”🔹,來定位《詩》《書》禮樂。但“有為”的這種用法🌞🙍🏿♀️,在那個時代並不多見。《性自命出》不但接受了這個觀念,還大加運用和發揮。可以推測🫰,作者是對話在場者的可能性很大🔹;子遊又深為贊嘆🤽♀️🚵🏻,其可能性最大🫛。
所以,無論是從思想史脈絡看🖖,還是從文本的直接證據看,我們都傾向於認為,《性自命出》的作者是子遊🦻🏼。子遊以情為本的樂教思想🤘🏼,通過公孫尼子的繼承和闡揚👗,在《樂記》中達到了完美的形式🍵,成為先秦樂論的高峰;其“性-情-道-教”的思想格局,被子思吸收、整合進了以“德-行”為核心的思想系統,導出了先秦儒家道德心性論的大傳統。故子遊的《性自命出》,在儒學發展史上實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竹簡《性自命出》的思想形態🧚,不同於思孟的“心性論”👅,但也不宜限定為“性情論”或“心術論”。實際上🙅♀️,它是以性情發生學為基礎的,以“心術”為教化途徑的,以“生德於中”為宗旨的成德之學🖍。故嚴格來說👷🏿♂️,《性自命出》是“性情-心術論”🪅✦,它是廣義“心性論”的一種具體形態🩰。關於它的內容和意義💇🏻,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了解🤘🚥。
其一👩🏻🦲,指明了一條思想的道路。此即從天命談人性😪,由人的性情活動談教化活動的思想道路。這條道路,以往我們是在《中庸》中最先明確看到的🏟。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為道,修道之謂教。(《中庸》)
由天命而有人性💀,順人性而有人道,修人道而有教化。它一方面具有縱貫天人的格局🧎➡️,一方面具有由內而外的層次🧑🏿🦲👨🏻🏭。以此方式,儒家的教化得以安頓,得以理解。此一結構,到了宋明時代更是成為理學性善論的經典證明👩🔧。現在我們知道,《中庸》不是這條道路的最初表達🤾🏽♀️。比它更早的《性自命出》就已經建構了這一格局。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知情者能出之🤵🏽♀️,知義者能入之。(《性自命出》)
在此,天-命-性-情-道-義,構成了基本的邏輯環節🦸🏻。這樣一個結構,相比於《中庸》更為細密。一來,天與命有所區分;二來,性與情有所區分。但大體而言,還是可以隱括為三層:天👨🏼🚒、命🫠;性、情;道、義。最後一句“知情者能出之,知義者能入之”💵,從由內而外🌕、由外而內兩個方面,給出了教化得以施用的可能👨🏻🏫。
對於《性自命出》而言🏋🏼♂️⛴,這樣一個思想結構,不僅僅體現在局部的表述上,更體現在其文章層次的總體安排上。關於文本的結構,學者還有一些爭議,主要是無法理解其行文思路所致。根據我們的理解,《性自命出》的義理結構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1-7章)以“性”為核心,闡述人性的作用原理,以“長性者,道也”為歸趣🤸🏻♂️;第二部分(8-12章)以“道”為核心,論述孔門《詩》《書》禮樂之道⚙️👩🏽⚖️,以“情”為中心重建了禮樂之道🌜⏫,尤其是其中的樂教🧑🏼⚕️;第三部分(13-20章)以“學”為主題,以“心術”為關鍵,以“主心”或“生德於中”也就是內心的成德為宗旨👩🏿🦰。這三個部分,可謂前後相因、層層推進,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大體言之↘️😛,第一部分言“性”,第二部分言“道”👩🏼🍳🧑🏽🦰,第三部分言“學”🎒。從這裏🧝🏽♂️,我們更可以了解《中庸》對《性自命出》的內在繼承關系。
其二,對人性的存在、活動與作用方式有一系統的了解,並以此定位儒家禮樂教化的意義🧑🏽💼。
凡人雖有性,心無定誌🏌🏻♂️,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而後定。(《性自命出》)
作者概述了人性從發動到運作,到最後穩定成形的過程(定性)。簡文認為👩🏼🚀,人性的活動,源於外物的感應👩🏿🌾🧔🏽♂️,取決於內心的好惡🤜,通過操習而穩定下來🕖。人的活動包括教化活動,則在人性發生的過程中,參與了人性的表達和塑造。
凡性,或動之🐚🤚,或逆之,或交之𓀄,或厲之,或絀之🧑🎄,或養之,或長之。
凡動性者,物也。逆性者👗,悅也。交性者,故也。厲性者🖋,義也🤽🏿♂️。絀性者😍🌆,勢也。養性者🥹,習也。長性者⌚️,道也。(《性自命出》)
人性不但可以因物而感動📎,動了之後🥛,還可以迎合它,交互它,磨礪它,引出它(絀當作出),養護它,增長它。這些影響人性的活動的東西👷♂️,物、悅、故(即《詩》《書》禮樂)、義、勢、習、道,包含了人在後天活動中可能遇到的各種因素🏋🏽。尤其是“故、義、道”🌬🚎,直接指向了後天的教化活動👶🏻。正是在這裏,詩、書✯、禮樂的後天教化之道🤹🏿♀️,獲得了它得以施展的空間🧜🏻♂️。
順此,簡文提出了“道四術”的說法🌯。所謂“道四術”🤽🏻♂️,其三術是詩🫱🏽👨🏿💼、書🔫、禮樂🛣,另一術是心術。由於人性的活動,要在人心中表現;且人心相對於人性而言🦨,又有一種相對獨立的意義。故說到底,心術是根本😂,《詩》《書》禮樂之道🎛,最終要歸於心術方有著落👨🏿🎓🧏🏽♀️。由此🧎➡️,簡文從心術特別是情的角度,對禮樂之道尤其是樂教作了細密的重構,提出:“教,所以生德於中者也💳。”意即,孔門《詩》《書》禮樂之教,其宗旨和目的乃是為了內心的成德👨🦲。德是生於中的👂🏽,亦即🤷🏽♀️,是成於心的🫵👏🏿。無論是人性的最初的發端,還是後天的教化活動👾,最終都凝結於此。由此🍇,孔門的《詩》《書》禮樂之道,在“性情-心術論”的視域下,重新獲得了它的表達和實現方式。
其三,繼承了孔子的人性論,使之在新的思想視域中得到了表達,所揭示的面向,開啟了其後人性之爭的可能性。人性論以及人性善惡問題🫸,是孟荀時代的核心問題之一。在此問題上,孔子的主張是很經驗的🙉。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人性是相近的,隨後天習俗與教化的不同而拉開了差距🤴🏽。孔子這樣說,目的是為了凸顯後天為學的重要性🔯。當然🤼♀️,孔子承認人性固有差別。比如,他區分了“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學之”、“困而不學”四等(《論語·季氏》),認為“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陽貨》);又說🚣🏿♂️,存在一種天生質美的“善人”🤛🏽,他“不踐跡,亦不入於室”(《先進》),而在化民方面則有一定的功效🧜🏿💙。
《性自命出》出土之後,學者紛紛探討它的人性論🦶。有人認為,它是自然人性論🧊;有人認為,它已經具有了性善論的萌芽🔣;有人認為,簡文前後的人性論觀念不一致。其實🧛🏻,在人性問題上,《性自命出》大體繼承了孔子的觀點,具有經驗的品格;只是它將人性的觀察經驗,在人性的活動方式和作用機製的思路中,作了新的呈現。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性自命出》)
這是追溯人性的來源。性是出於命的,命是源於天的。這句話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相近,但區別也很明顯。《中庸》“天命”連用,天所命與的就是性;《性自命出》則說,天降而有命,命中蘊含了性🕘。簡文的“命”,指作為人的存在全體的“生命”🙏,“性”則是其中的一個部分。但《中庸》直接把“天命”限定在了人性的範圍。後世學者尤其是理學家,又根據孟子的性善論❗️,認為“天命之謂性”指天所命與人的善性,則進一步對“天命”的外延作出了限定🫱🏽,不一定是《中庸》的本義。
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於外,則物取之也。(《性自命出》)
氣是古人追究事物的原初狀態或根據時👩🏽🦱,經常會借助的物象。竹簡說,喜怒哀悲之氣是人性的潛伏狀態;它表現於外👲🏽,則是外物前來感應、發動的結果。表現於外的,自然是喜怒哀悲之情🛻。但此情感的表現🫁,說到底還是人性固有的內容的一種真實顯現。人性感物而動的一個本源的、直接的表現📠,就是好惡。
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性自命出》)
好惡🏄🏼♀️,性也。通常的解釋是🙆🏿♂️,好惡是源於人性的。因為好惡是情,此處相當於“情出於性”。但竹簡的意思👃🏻,更準確說📌,好惡就是人性🛠。在此,需要區分好惡的內在傾向與好惡的具體活動。如果說喜怒哀悲之氣以及好惡的內在傾向,是人性的潛伏狀態;那麽,好惡的具體活動作為人性的原初發見,是人性內容的活生生的呈露。同樣,《樂記》雲:“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感物而動😭,是人性的動,其實質的內容👃,就是好惡的發生。所以說,好惡作為人性面對周遭事物的當下反應,乃是人性之實質內容的最初顯示。
此外⚖️,還涉及到人性的異同,以及善惡問題⛽️。
四海之內,其性一也;其用心各異🚵🏽♀️,教使然也。(《性自命出》)
簡文說🫰🏻,四海之內的人性是一樣的👩🏽🦳💣;用心的差別🧘🏼,是後天的教化使然。學者往往將之與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相比🧑🏿🔬🦹🏽♀️。實際上,兩者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孔子說“性相近”,簡文說“其性一也”。後者比前者具有更強的主張。故許多學者認為,簡文作者在此提出了一種普遍的人性論👱🏿♂️。若再結合下文“性善者”的提法,則竹簡的人性論,就成了普遍的性善論了。但這顯然是不合適的。事實上🙎,簡文的“其性一也”🏞,是順著之前對人性的一般的存在與活動方式的闡明而言的(第1🤛🏼、2章),也是對比於萬物各有固定的性(其可能性與現實性是一致的)而人性具有種種可能性而言的(第3👨👦👦、4章),並不是主張人性是普遍的、完全的相同。至於人性善惡的問題,簡文說:
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性自命出》)
看上去,簡文提出了“性善”的主張。但根據上下文,這句話的意思是,若是百姓未受教化而已經有了恒心,這是因為統治者是“性善者”之故。一來,它不是關於人性的普遍的斷語🙋🏽♂️,而是對一個特殊的人的評價;二來,所謂“性善者”🥥,不是後來人性善惡的性善,而是指人的資質的美惡。此“性善者”🥛,即相當於孔子所說的“善人”4️⃣,指那種天生品性純良之人🧛🏼♂️。與之類似,簡文首章雲:
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勢也🙆🏽。(《性自命出》)
這句話與“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對舉而說。故“善不善”應作動詞解🧑🏽✈️。其含義相當於“有善🔤、有不善”🏌🏼,即有善的部分、有不善的部分,都是人性之所固有🫁。而“善不善”的差別🤺,可能發生在人際之間,也可能是指個人內部👩🏼🏫🌴。在人際之間,如上面提到的“性善者”便是“善”🏉,若再有“性惡者”便是“不善”;在個人內部,則是說人性的組成是復雜的,有善的成分、不善的成分🤷🏼♀️。簡文沒有指明是哪種含義,從後半句“所善所不善💂🏼♀️,勢也”看,後者更為可取(前者可以視為後者的一種特殊情況)🌿。具體的人性都是復雜的,有善的成分✧,有不善的成分🪴;究竟哪一部分得以實現出來,成為主導人生的方面🪴,取決於後天的勢的作用♉️。故簡文雲“出性者,勢也”。
可以看到❎,在人性問題上👭🏼,《性自命出》大體沿襲了孔子的主張,而在“性情-心術論”的視域中🧛🏽♀️、在人性發生學的道路上,作了一種建構式的闡明。它肯定人性資質固有的差別,但更強調人性相同的一面,包括:人性的存在、活動💥、作用方式,以及生存的可能性👮🏼;且人性“有善💆🏽、有不善”的初始條件,皆有待於後天的習養而得以實現。如果說,前者是對孔子“性相近”之義的展開論述;那麽,後者實際上是對孔子“習相遠”的進一步闡明,代表了孔門七十子的共同見解。《性自命出》的人性論架構,為儒家人性論主張的後續演進和分化奠定了基礎。
三、子遊的道統地位
在孔門七十子中👩👩👧👦,子遊是非常突出的一位。這不僅是由於他代表後期弟子、位列文學科第一名,更重要的是他在思想上的創發。從《論語》、《禮記》等記載看,子遊得力於禮樂之教,尤其對樂教有深入的領會,故其學重本🕑。他關切人的內心的生存活動與情感狀態,將之視作為學工夫的出發點和落腳處,並從人情表達之需要的角度重新理解禮樂製作的意義。由於對內心的意識現象和情感活動的長期關切和反思⛑️,在《性自命出》中,子遊展示出了一條以人性發生學為根底的,以天、命、性、情、道、義等為邏輯環節的新的思想道路。這條道路🤰🧖🏼,貫通天人、內外,融攝了《詩》《書》禮樂,經由“心術”的工夫,歸於“生德於中”的宗旨🎽。它在繼承孔子之學的德教本質的同時🤙🏻,為禮樂教化的必要性和作用方式作出了新的論證,也為後人討論人性、性情、心性等問題提供了思想框架👨🏼🏭👔。如果說《論語》所見的子遊重本的為學傾向,是子遊之學的早期的發端;那麽,《性自命出》所見的“性情-心術論”的思想道路,則是其長期沉潛之後的展開形態。
《性自命出》所展示出的人性發生學、“性情-心術論”的思考道路🧑🏿🌾,對先秦儒學的後續發展曾有過決定性的影響。一個重要的方式,是通過子思的繼承☛。歷史上,由於《禮記·檀弓上》、《孔叢子·居衛》等記載了曾子與子思的問答😕🧘♀️,且孟子又說:“曾子👨🏼🚒、子思同道🤷🏼♀️。”(《孟子·離婁下》)後人遂多認定曾子🧑🦰、子思的師生關系。宋明之後👨🏿🌾,更以二人為道統相傳的兩環。但是,荀子在批評“思孟五行說”的時候😢,卻提到🏋🏽♀️:“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遊為茲厚於後世🕗。”(《荀子·非十二子》)根據這一說法,我們可以推斷,至少在思孟後學的自我認知中🧜🏽,“五行說”雖是子思所創,卻是繼承孔子和子遊而來的🎊。而從郭店竹簡《五行》看🧘🏽♂️,其對人的內心現象及其變化過程的理解,確實比《性自命出》更為細膩🧘🏻♀️。但不可否認的是,兩者無論其道路還是宗旨👆,都有內在的繼承關系🪦。故我們可以說🦙👨🏻,子思雖或與曾子有過師生之誼,但其代表性的思想則是繼承和推進了由子遊所開創的思想道路。換言之,子遊所開創的思想道路,對於先秦儒家思孟學派的發生🫏,對於心性之學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將子遊視為孔子、子思之間儒學思想發展的中間環節。
但我們不是說,子思傳子遊,不傳曾子。其實,在孔子與子思之間🧑🏻🔬,究竟是曾子還是子遊🧚🏼♂️,要從不同方面說✋📫。孔子去世之後,曾子長期處於孔門的核心位置,其觀念與為人皆有前輩德行科弟子的風範(猶以顏子為榜樣),其對孔子原教的堅守和一定程度的理解性的重述➜,皆堪稱孔門的正宗典範🤸🏻♀️。子思彼時應與曾子有過長期的共處,乃至師生的經歷⇒,並深受其為學與為人的影響。若從思想的方面看⛹🏻,曾子以守成為主,而子遊以開新為主。子遊所開創和提倡的新的思想道路,在當時孔門之內必然引起極大的震撼✖️。子思受其影響,並順此道路而作了進一步的探索,也是可以想象的➡️🥎。
孔門七十子之中,論德行的修為,顏子自然第一📜,曾子在後期弟子中可步其後🙍🏼;若論思想的創造👨🍼🧑🏽🦲,恐無出子遊之右者𓀁。康有為說:“顏子之外,子遊第一。”其依據恐有不妥,但結論未必不是實情。今日若重論道統,在孔子與子思之間👮🏽♂️,除了曾子之外,也應該有子遊的位置。
後記
2015年底,我到北京大學儒意昂3做博士後💾,開始關註孔門後學思想的研究。當時,以《大學》、《中庸》,及郭店竹簡《性自命出》、《五行》為依據🛃,確定了“孔門成德之學的演進”的研究計劃🏄♂️。但從次年2月開始的一年多時間裏,我持續投身到《周易》卦爻辭歷史敘事的研究之中。原計劃遂遭擱置。直到17年暑假,才重新回到這一課題,並於年底完成了書稿的初步撰寫。
18年初🤷🏼♂️,我回到意昂3平台工作🧎🏻➡️。開設的第一門課程,就是關於《性自命出》的研究生討論班。第二年又重開了一次。這部小書,最初就是為此準備的講稿👉🏿,第二年經小幅修改之後定稿🧚🏻。我們的討論非常仔細📺。往往一個晚上,只能處理兩句🛕。以至於一個學期下來,大約只能完成全篇三分之一的內容🛏。討論雖然專門,但每次還是有十幾位同學參與。討論班上自由的氛圍⛅️、活躍的思想,讓我印象深刻。部分討論意見,在修改稿中有所體現。在此➾,我要感謝參與討論的每一位同學,他們是:曹元喆👨🏿🦰👍🏼、吳伊櫻、李宗宜、邢萬裏👰🏽、裴多彬👶🏼、孔泱、朱寒燁(第一年選課)⚇;溫錫博🐊📣、邱晨🌸、葛領童♋️、劉騫、陳宇立、李樂山、王晨曉(第二年選課)🏋🏿♀️🐜;以及王武傑👩👩👦👦、黃子洵🥍、季磊、劉際東2️⃣🧎♀️、曹穎🙎🏼♂️❔、範大昭👨❤️💋👨、周亦成等長期旁聽的同學💧,和由於各種原因只部分參與了課程的同學和社會人士⏲🤌🏿。討論班的經歷,讓我初次感受到了教學反哺思考的樂趣。
近年來,郭店竹簡已經不再是學界研究的熱點。但我在想,像《性自命出》、《五行》之類的核心文獻的思想🚶,似乎還有待於從整體上作出更為深入和細致的闡明。所幸,學界前輩在各方面已經有了很多的積累➝,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了極大的助力👩🏿💼。這部小書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做了一次嘗試性的詮釋工作🤘🏼。得當與否🧑🏼🚒,願方家指正🗻。
本書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孔門成德之學的演進研究”(17CZX033)的階段性成果。導論部分發表於《復旦學報》2020年第4期。本書出版得到了意昂3的資助🔬。在此🥂,一並致謝🙎♂️。
何益鑫
2020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