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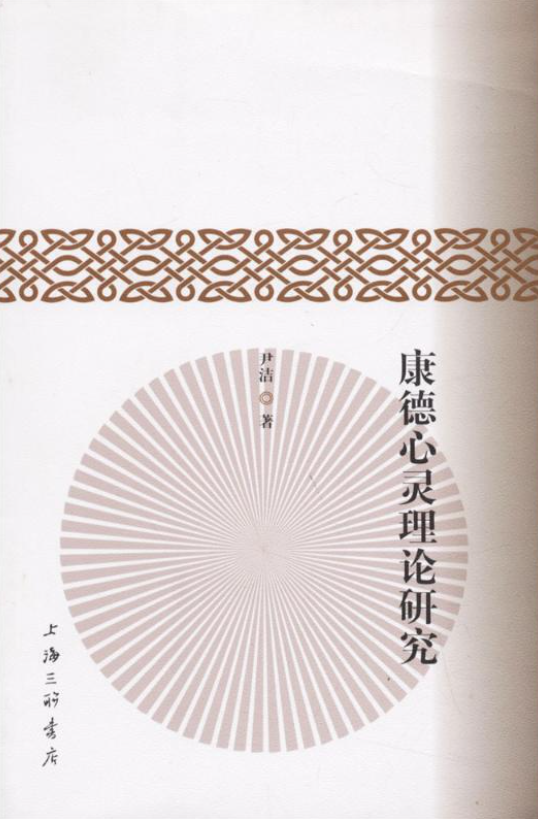
書本信息
作者:尹潔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出版年月:2018年4月
ISBN:978-7-5426-6043-5/B.538
作者簡介

尹潔,博士,現任意昂3青年研究員、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生命醫學倫理學、醫學哲學和康德哲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2006年獲意昂3平台醫學學士,2009年獲意昂3平台哲學碩士,師從張汝倫教授🧚🏼。之後獲得紐約州立大學Albany分校哲學系博士全額獎學金,師從康德學者Robert Howell、實用主義哲學家Robert Meyers和心靈哲學專家Ron McClamrock,於2013年獲得紐約州立大學Albany分校哲學博士學位👩🏻⚕️。近期研究集中在醫療公正和神經倫理兩個方向上🚜。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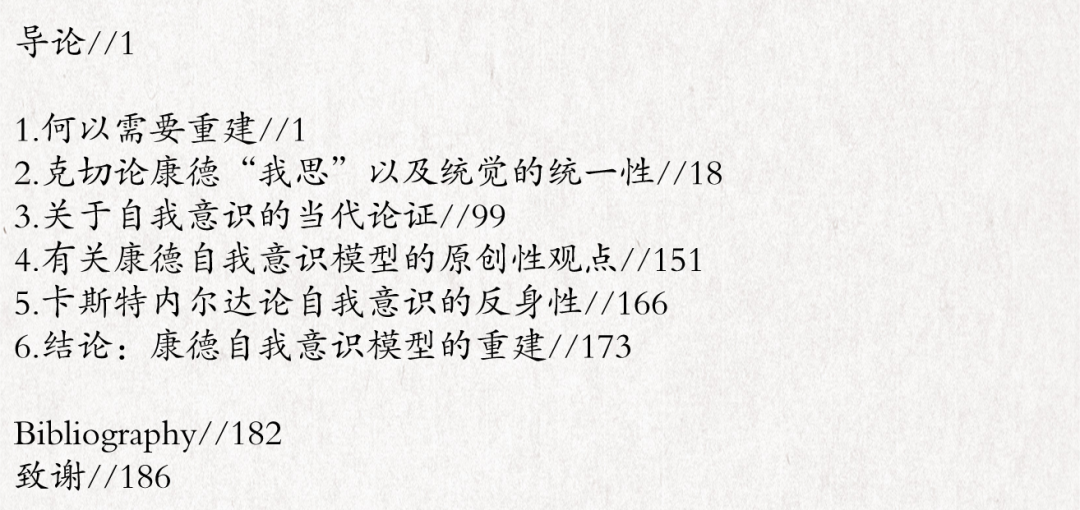
導論
促使我寫作此書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到底有沒有關於自我意識的一個合理的觀點?如果有的話,那麽我們以何種方式才能挖掘出相關觀點的魅力🫏?當然,我還試圖進一步探討,在何種程度上🤶🏻,康德的觀點能夠啟發當代分析哲學家關於自我意識的討論🫲🏻。這些討論始於兩個由Robert Howell在其2006年的論文中提到的問題。問題(A):究竟“我思”這個表象👸🏼,如何能夠,指涉性地♙,表象出“自我”🟪🧑🏿🔧,從而將其帶入我們的思維意識當中🙆🏽♀️?問題(B):究竟,“我思”或“我”這個簡單的表象和對自我的一個指涉🎍,何以能夠產生真正的、第一人稱的自我意識?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將通過詮釋康德觀點和補充進當代最新文獻成果的方式,重建康德的自我意識模型。簡言之🧙♀️,我將試圖發展出一個康德式的自我意識模型,而要構建這個模型需要借助於來自當代分析哲學文獻的工具,從而能夠將康德哲學的細節詮釋得更為明晰🧙。
當代關於自我意識的討論,按照格特勒(Brie Gertler🐩,2011)的觀點,集中在討論在一個可能的自我意識片段裏面,自我的本體論特性到底是怎樣的🫔👨🏿🦲。也就是說🚔,在外部世界中,究竟自我在本體論意義上優先於一般的物理對象👱🏼♀️,還是由於其時空特征🦵🏼,自我其實也只不過是一般物理對象之中的一員?另外一個問題則是🪤,在同一個自我意識的片段中👨🌾,何以自我同時是意識的主體也是對象 🖤?
我著重要論證的是🚴🏽♂️🫲🏼,康德有一個更好的方法看待自我意識問題👩🏼🍳,從而使得他不用判斷在一個自我片段中,自我到底應該被看作首要地是主體還是對象,這是因為在康德的模型中🧞♀️,一個人擁有第一人稱的自我意識當且僅當在一個意識片段中的自我意識的反身性得以可能的時候才是可能的🧑🏻🦞。我同時也論證說🚴🏼,主體和對象的二分法的應用是自我首先是主體還是對象之爭的緣由,並且任何一個站得住腳的自我意識模型必須要回避這個二分法。
我並未采取一個笛卡爾式的二元論框架作為這個模型的形而上學基礎,相較之下👩👩👧👦🏊🏼♀️,我選取了用“反身性”來構建自我意識的模型♕。更精確地說,我將重點強調Howell的這一觀點🐇,即🪂,直接指涉理論與康德關於我思 和自我意識表象的觀點最為相關,同時,我也會強調卡斯特內爾達(Castañeda)關於自我和自我意識的核心觀點,即“自我意識在通過oneSELF想到ONEself的思維片段中被實現”(Castañeda,1990,第120頁)𓀍,也就是說,在任何的自我意識片段中,一個人通過himSELF來指涉HIMself🧒。在這裏🚉,HIMself指的是一個人以從物(de re) 的方式指涉之物🧞♂️,也就是說🧘🏼♂️,這個人在指涉此物時並未代入對於任何內容性的思考,himSELF指的是一個人在以de dicto的方式(也就是以可與其他說話者分享的方式)來指涉HIMself.
初看下來,似乎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關於“我思”的討論和Castañeda關於自我意識的內在反身性(internal reflexivity of self-awareness)之間並無直接關聯。然而,我的確認為Castañeda的內在反身性提供了一個最好的呈現康德那極具原創性的自我意識模型的框架。在“範疇的先驗演繹”中👩🏽💻,康德論證說先驗統覺的統一是綜合先天判斷和自我意識的必要條件。
在本書的第一部分✭,我將勾勒出康德關於自我意識觀點的輪廓💇🏿♀️,比如像“我思”🙆🏻👩🔬,“內感官”和其他相關論題。然後在第二章中,我將討論最新關於先驗統覺的統一,也就是克切(Patricia Kitcher)所謂“康德之思者”。再之後,在第三章中🙅🏽♂️,我將分別討論當代兩位分析哲學家舒梅克(Sydney Shoemaker)和伊萬斯(Gareth Evans)的自我意識學說;在討論這二位時,我的目的是想得出一些啟示性的觀點從而能夠代入對於康德的解讀和重新闡釋當中去𓀑🦁。在第四章中,我重點探討Robert Howell是如何用當代語言哲學中的direct reference theory(直接指涉理論)來詮釋康德的“我思”概念🧝🏽,強調Howell的理解在何種程度上契合康德的文本並且我個人對於這一詮釋的評論和回應。在第五章中0️⃣,我著重探討Castañeda的內在反身性概念以及這個概念如何可以作用在解釋自我意識上。在第六章也就是結尾章,我將以前面幾章的鋪墊為基礎,提出我重建的自我意識模型👩❤️💋👩🧎🏻➡️。
我的觀點大概是這樣的:在這個基於Castañeda觀點的康德自我意識模型中👬🏼,自我意識之所以得以可能,是因為有一個先驗統覺的綜合性的行為。這個發自先驗統覺的綜合性行為,既能以一種de re的方式反過來指涉出那個思維主體,又能以de dicto的方式將其經驗認知全部歸結於那個思維主體。自我意識的可能預設了以上這些。
我希望在正文的詳細闡述中🌡,我構建的這個模型的新穎性能夠慢慢顯露出來。簡單地說,首先⛹️♀️,這個模型能回答前述的問題(A)且不需要面對主體——對象的二分法🧍🏻。其次,這個模型暗示了一種我們可以借以辯護“無所不在命題”(ubiquitous thesis) 的方法,比如說,我們可以退一步說,並非是一個真正內容形式皆備的第一人稱的自我意識 必須預設經驗認知😒,而是一個第一人稱的形式的自我意識預設了經驗認知。這樣一來🤱,修改過後的這樣一個版本的“無所不在命題”(ubiquitous thesis)仍舊成立,而且同時我們還能保住意識並不預設自我意識這樣一個結論 。
我所得出的結論,具體而言如下。對於問題(A)🕣,我的回答是:由先驗統覺的統一所執行的綜合行為導致了經驗認知的產生(當然這也需要一個人同時也得到了來自被動的感官所獲得的直觀雜多)👩👧👦,並且同時這些行為也指涉出或者挑選出一個思維的主體,這個主體擁有一個純形式的意識結構,並且因為這個先驗統覺的反身性,綜合的行為本身僅僅指涉出或者挑選出那個思維主體而無需激發產生任何完整的🛎、鮮活的第一人稱自我意識🧚🏽♀️,這是因為此時關於自我的內容還沒有被呈遞給被指涉出來的那個思維主體e🚣🏼♂️。Castañeda所認為的真正的第一人稱自我意識,需要一個從無自我的意識到一個有自我的意識的轉變過程,並且這個無自我的意識或者說純形式或結構的自我意識,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先天形式或結構的圖式,該結構圖式僅僅能夠把那個思維主體指涉出來。而關於這個被指涉出來的思維主體🥤,按照康德的看法🚊,我們什麽也不知道,我們並不知道它的本性,不管是通過這個意識的純形式還是通過其他的什麽方式都無從知曉。按照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裏面所說的👩❤️💋👩,直觀和知性的先天純形式構成了自主的認知主體的本質。像如此這般的自我意識還不是第一人稱的自我意識🦸🏽♀️,因為在此意識當中一個人並沒有在思考他所指涉的那個HIMself。僅當一個人能夠通過oneself指涉ONEself 的時候🎨,第一人稱的自我意識才能得以可能🫄🏻。
對於問題(B)的回答則要求我們變換一下視角,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得脫離這樣一個窠臼,即總是認為第一人稱的自我意識是在第三人稱的意識上加上某些第一人稱的要素或模式從而得以可能的。這似乎與Evans所持有的觀點相矛盾👷🏿♂️,因為Evans說為了能夠歸結任何的精神的或者物理的謂詞,一個人必須得能夠將謂詞也歸結給他人,而這就意味著自己只能把自己視作與其他一般對象沒有什麽本質性的區別。然而👞,我還將采納所謂第一人稱的意識是第一人稱自我意識的一種原始的特征或模式,並且,他也不能被還原為第三人稱的意識,但這並不意味著第一人稱的自我意識是不可解釋的😵💫。如此這般的第一人稱意識僅第一人稱的自我意識由通過某個人以himSELF去指涉HIMself而產生的時候才可能被產生,也就是說,“我”之表象僅當第一人稱的自我意識片段出現時才一道出現。簡言之,如果沒有第一人稱自我意識的片段,就沒有“我”之表象 。再者🧏🏻♂️,在如此這般的自我意識裏面🎇,自我歸結的方式不同於當一個人歸結精神的和物理的謂詞給他人的方式,盡管2️⃣🏟,就像Evans所強調的那樣🛄,任何的歸結都需要以一個人有能力能將自己或他人置於個別的時間空間中🦢。而至於為何在時間空間中占一個位置的必要性並不一定意味著第一人稱的自我意識預設第三人稱的意識🟦, 我的回答是康德在先天直觀純形式(包括時間和空間)上的先驗論證,已然給為何將一個人置於個別的時間空間中對於達成自我意識而言是至關重要的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說明,這個說明的存在使得將第一人稱自我意識往第三人稱意識的還原顯得沒有必要。
正因為有這樣一個模型🚝,我們可以領會這樣一個觀點,即第一人稱的自我意識當且僅當第一人稱的意識出現時才出現。我在這裏使用在狹義上使用“第一人稱的自我意識”這個詞,也就是說👩🦯➡️,在此意義上🧔♂️,當一個人能夠使用第一人稱代詞“我”的時候,他同時也意識到他所使用的這個“我”只指涉他自身而不關乎其他人🟧。這也就是說,僅當我的自我意識和經驗認知同時由綜合行為和先驗範疇的應用(當然同時需要來自被動感性官能的直觀雜多)達成的先驗統覺的統一而得以可能的時候,我才能擁有這個有“我的”特征的經驗。
因此,結論並不簡單地是“我思”表象產生了第一人稱的意識,而是由先驗統覺的綜合行為通過其以無屬性方式指涉出一個自發的思維實體e從而產生了自我意識🔔,但實際上這個實體e並不真的存在。真正存在的是思維的原初主體以及由“我”之表象而產生的這個主體的個別思想,這個思維主體能產生統覺性的思想並且在此過程中,任何有關此主體的本性都未能被揭示出來。正如我在第六章中將要揭示的,統覺性的思想通過生成一個反身性的思想;這個思想我叫做標記M🧗🏿♀️,因為它能夠作為統覺性思想的一個真正的內在的第一人稱的自我表象👆🏻。標記M當意識綜合內感官和外感官的雜多時由統覺性的意識產生,並且這個標記M能夠以一種指涉性的方式為統覺性的意識起作用😹🤾🏿♂️,從而在我們看來標記M表象除了一個實體e🫵🏼,而所有內感官雜多的元素都歸於這個實體e。然而🌉,在我看來✶🤦♂️,真正存在的其實就是這個標記M(M是一個在我們的意識中來了又去的過渡性標誌),並且這個e就是一個虛構的實體🩻、一個由標記M指涉出的東西。當統覺性的思維綜合內感官和外感官雜多而產生這個個別的思維標記時,統覺性的思維也因此向自己呈現了一個虛構的結構🤽🏻,在此結構中所有內感官雜多的元素都歸屬於一個個別的實體e🧑⚕️。因此這樣看來,這個個別的實體e其實就是康德的經驗自我,一個個別的擁有經驗認知的人🕵️、一個通過其精神狀態且通過此種綜合,就能得以知道一個外感官的對象有如此這般的特定的屬性。(比如說,通過此種綜合🤳🏼,我,尹潔👰🏼♂️,就能知道現在我看見一份論文擺在我面前。)一個真正的、第一人稱的自我意識由此被達到🤹🏽,但是實體e仍然是虛構的,我們僅僅將其看作是我們假設的“我”之表象的指代之物。簡言之,實際的情況是我們將所有雜多元素都當作是屬於虛構實體e的,也就是“我”之表象的指代對象📟、那個被假設的經驗自我。
結論𓀊🙆♂️:康德自我意識模型的重建
在本章裏,我將給出我自己關於重新建構的康德式自我意識模型。我的模型采取了霍威爾的直接指涉詮釋和卡斯特內爾達的反身性作為其本質性的框架𓀘,與此同時,在一種較為寬泛的意義上,與我所解讀的康德可能試圖表達的意思相吻合🧑🏽🎤,尤其是從克切角度的康德詮釋較為吻合🧑🏿🚀。我將論述我的這一模型在何種意義上是康德式的,以及在何種意義上它能夠回答霍威爾的兩個重要問題而不至於卷入我前面指出的當代論爭關於此的常見錯誤之中。
6.1. 一個嘗試性的對於克切論述的辯護
根據我的詮釋🧑🏿✈️,康德的我思蘊含了一個理論,這個理論可能能夠被重建進一個自我意識的模型裏面🤷🏽,通過引入自我意識的反身性模型的方法𓀈。以這種方式行進應該能夠提供一個好的理論用於解釋究竟由我思產生的自我意識是如何可能作為一個認知過程,以及為什麽這樣產生的自我意識是第一人稱的🐦⬛。對於康德而言,統覺的先驗演繹產生了經驗性認知🧭。克切(2011,160頁)在其書中認為理性-經驗性認知(RE-cognition)和自我意識互相蘊含彼此。她寫道“先驗演繹的那一為了統覺之統一的論證在於對於理性-經驗性認知的必要條件的檢視……核心的議題是理性-經驗性認知和自我意識互相蘊含彼此。“(克切2011🫃🏿👉🏼,160頁)然而,在斯坦(2012)看來,克切試圖證明的是統覺的先驗統一和理性經驗性認知互相蘊含彼此,並且他進一步論證說克切的論證最多只能證明這個論斷的一半👐🏿,即她只能證明,回溯性地👳🏼♀️,基於理性-經驗性認知是可能的🚍,統覺的先驗統一必須在場✥。換句話說💣,斯坦認為克切不能證明統覺的先驗統一必然蘊含理性-經驗性認知✋🏽。但對我而言似乎克切並不外顯性地認為統覺的先驗統一蘊含理性-經驗性認知,基於我在前文中從克切書中第160頁的引述來看。
除此之外,我還認為斯坦忽略了一個克切論點的重要維度🤦🏻,也就是,她的這一觀點,思者在某種程度上由思考行為構建 🥄💪🏽,因此通過查看一個人思考的內容,他能夠知曉這個人作為一個思考存在物是什麽。盡管當斯坦論證統覺的先驗統一並不必然蘊含經驗性認知的時候他是對的,這個立場近似於大部分康德學者的共識🍚,即🪬,範疇的先驗演繹意圖要揭示先天範疇的客觀有效性的目標實則沒有達到,但是斯坦誤讀了克切的目的📻。
克切論證的不是範疇的先驗演繹必然蘊含經驗認知💂🏼♀️,而是我們知曉自身作為思維主體的方式在於我們組織那些從被動感性中得到的東西🧓🏻,即通過將先天要素加入直觀雜多的方式。換句話說,克切認為🚶,思者的本質以某種方式被思維的活動所揭示🧑🏼⚕️。首先🚴🏿♂️,我認為克切非常清楚地知曉,範疇的先驗演繹並不必然蘊含經驗認知。在她對於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的文本解讀中🧝🏻,她展現了統覺的統一是最為基礎性的主題,這一主題康德既在“範疇的先驗演繹”中也在“謬誤推理”中強調了。我將她對於這一點的認識當作一個提示她可能對於某一觀點的認同,即,既然統覺的先驗統一是人類經驗中最為基礎性的要素,那麽更合理的是去認為先驗統覺才是對於經驗認知和自我意識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去堅持統覺的先驗統一和理性-經驗性認知互相蘊含彼此,這也被斯坦認為是克切持有的觀點。我認為如果克切只是說統覺的統一對於經驗認知和自我意識都是必要的話,會減少一些誤會。
因此如果要試圖為克切辯護其來自斯坦的反駁,我實際上建議了一個有關自我意識模型的正面論述🍘,我將把這個展現在下一節裏。我也將指出,盡管康德在B版中證明先天範疇的有效性失敗了👨🏿🎓,康德關於我思的探討無疑道出了有關自我意識的合理觀點💅🏻。
6.2 重建的自我意識模型
以最簡單的形式來描述我的理論的話就是:我認為先驗統覺的行為是反身性的且源自一個自發的思維主體。借助“先驗統覺”,我是指🧍,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提到的,思維主體產生此類思維行為的能力🚀。這些行為是反身性的,因為除了把握對象的熟悉感之外(思維行為把握類似於一些東西擁有這樣或那樣的特征),這一行為意識到其自身流出自(即作為被製造的和歸屬於,被錨定在)那個主體。只要它意識到或者甚至把握到主體作為一端使得其自身從中流出(即使它沒有把握到任何其他關於主體的本性🤹,超越由主體製造的事實),這一行為就可以被說成是挑選出或者‘指涉’出主體。同樣,我將這一把握本身當作或產生了第一人稱意識🫅🏻。(當我通過當前的思維行為🙆,思考擁有如此如此的特性的一些事情就是這一對於自身的把握,即把其當作源自這一主體)註意這種第一人稱意識並不自身需求或包含任何個別的、獨特的表象‘我’。這一行為並不將其自身把握為以第一人稱思考者其內容(即有些東西有這樣或那樣的特性)🧞♀️,通過把握任意第一人稱我之表象的方式,該表象隨後將其行為導向思維的主體🍺🧑🏿🏫。相較而言,這一行為的第一人稱性質簡單地寓於這一反思性把握當中,通過這一自身源自主體的行為本身。
由先驗統覺造成的這一行為因此經由這一反身性結構🧞♂️,產生了一種形式的第一人稱自我意識。但是只要我們僅僅以其對於自身的反身性把握來描述這一行為,這一行為就沒有任何特殊的內容(它把握任何特殊對象或者經驗性心靈的時候不是以其擁有什麽屬性的方式達到的)。這樣的內容僅僅在經由經驗而來的輸入以及外部或內部直觀雜多的綜合的情況下才會進入🦣。因此這一行為不是一個真正的第一人稱自我意識,至少不是在這樣一種意義上來談論,即作為一種把握了的🌝、確定地思考著特定內容的經驗型人格或自我的意義上🧚🏻。什麽叫思考著特定內容呢✧?比方說“我,坐在這裏且思考這篇論文中的材料🌡,看見計算機是開機的”。這是經由綜合行為產生的自我意識的形式或結構,這一形式或結構因此首先產生了真正的第一人稱表象和意識。但是這種自我意識綜合了內容(既綜合了外感官的也綜合了內感官的),這些內容是由同一個統覺官能在使用我剛才談到的形式的第一人稱以及使用範疇而綜合出來的。並且這一真正的第一人稱表象和意識目前第一次引入了,獨特的第一人稱我的表象🧝🏿♂️,這在卡斯特內爾達看來📰,是轉瞬即逝的。
這是我的觀點的一個簡單的版本🐻❄️,未免有點容易產生誤解。我應該再澄清一下👱♂️,即,在我的模型裏👨🏿✈️,自我意識和表象我是齊頭並進的。轉瞬即逝的我是第一人稱我之表象,但不是實體的我,他們並不與被指涉的那個思維主體我相等同,因為它們的本質還是表象而不是實體👨🏿🔧。
表象我是一個關於人類的原初事實,因為在過程的這一階段,表象我也這樣一種方式產生了🚴♂️,即在哲學探究的階段無法被進一步解釋。這一表象作為一種特殊的、外顯的精神性‘我’這樣的詞而出現(以一種將代詞‘我’的直接指涉理論應用於康德關於我思之思維行為的描述中) 🐩,這一詞反身性地經由其自身的產物而把握自身——並且將其自身把握為源自於思維主體以及也當作指涉出一個實體X🖕🏿,一個人所有的內感官表象都屬於這一實體X。
正如一個統覺的思維可以將其自身把握為源自思維主體一樣,它也可以產生一個單獨的、外顯的關於實體e的思想(並沒有多少關於它的進一步本質的思考),從這個實體e中,那一統覺思維的個別行為流出了。我的觀點是統覺式的思維外顯性地思考了一個特殊的精神性的標記(我們把它叫做M)🟤,這一標記一般用來以一種規則(R)暗示的方式來折射一個實體e🖖🏽,也就是,規則是M的產生自動地保證了M指涉那個實體e🦻🏼。統覺思維關於M的把握本身反身性地把握了這一事實,即,思維或標記M沿用這一規則且也指涉那個實體e🧑🏻🍳🐹。標記M在這裏是外顯的內在思維行為,並以一種第一人稱的形式表達在自然語言當中(“I”, “ich”, “je”, “ego”等等)。標記M是外顯的第一人稱表象。
然而🧒,從我在這個情形中看到的而言,事實上這裏沒有實體e真的存在。所有真正存在的知識思維的原初主體,這個原初主體產生統覺性思維且關於他並沒有什麽進一步的本質能夠經由這個過程被揭示或被知曉,連同經由標記M的產生的那個主體的個別思維一起。統覺性的思維產生了個別思維-標記M當其有意識地綜合了內感官和外感官內感官和外感官的雜多時(並且因此達到了🔊,比方說🏃🏻♂️➡️,一個特殊的認知諸如“我看見了我面前的這臺電腦”)🤨。我的建議是,統覺性思維當其綜合內感官和外感官的雜多之時🤸🏻♂️🚻,通過產生這一特殊的思維-標記,向其自身展現了一個關於那裏存在一個特殊實體e的虛構結構,所有內感官的雜多因素都歸屬於這個特殊實體e。那一特殊實體e就是康德的經驗自我,那個特殊的個人e(在我的例子裏,指的就是“尹潔”),這個人擁有所有這些知覺的和認知的內感官狀態🔂,所有的人經由這些狀態就能知曉外感官的對象擁有特定屬性(比方說💁🏽,知曉我在我面前看見了一臺電腦)。但是,實際上,確實沒有這樣的實體e。真正存在的全部只是兩組東西🙅🏼♂️:(a) 當我們在綜合直觀雜多的時候💂🏻♂️, 我們關於思維標記M的轉瞬即逝的產物系列;(b)與我們這些轉瞬即逝的思維標記物M們相關聯的👱♀️,所有真正存在的也只是有關諸e實體的系列的轉瞬即逝的諸種虛構(經驗自我,那個叫“尹潔”的人)👳♀️,這些標記物指涉這些實體並且實際上擁有這些我們在綜合的諸表象。
在做好以上這些預備性的解釋之後,這裏我提出一個有關我重建的自我意識模型的總結,這包含以下三個階段:
過程的第一階段:經由思維的統覺行為,當然這是反身性的,我們能夠意識到思維的這一行為源自思維x的主體。這一意識是這是真實存在的——思維行為確實以此種方式源自於思維的主體。所以思維x的主體也真的存在🌙。思維主體由這一思維行為,經由這一對於思維行為本身源自此x這一事實的反身性把握而被指涉出來。因此以此種方式我們有了一個開始🤾🏻,在這一反身性思維行為的第一人稱類型的意識中,盡管尚不是完全的🐄、真正的第一人稱意識🫁,即類似於我們在使用表象我去以第一人稱方式思考自身的時候所獲得的那種意識(作為經驗性的人♗,那個叫尹潔的人👩⚖️,等等——因為僅僅是思維x的主體的話還不是一個人格人;我們除了知道統覺性思維的反身性行為源自x之外並不知道更多𓀆。)
過程的第二階段:然而♖👩🏻🦽➡️,在以此種方式把握這個思維的主體x的時候🤜🏽,我們未能把握關於其本質的東西——比方說,形而上學的或者其他的🧛🏻♀️,等等。對於我們而言思維行為源自的就只是x而已🤟。思維的行為本身(不是思維的主體x,而是源自思維主體x的那個思維行為)才是那個擁有純粹形式結構的東西,在這種意義上關於實體和過程的本性即關於那個x的本性,關於思維行為的流出🎇,即被包含在思維行為和其流出之中的👶🏻🪠,我們都未被告知任何信息⚾️。
過程的第三個階段:至今為止,我們沒有一個完全意義上真正的第一人稱意識或者任何外顯的表象我。我們沒有意識到作為人格的思維主體x(人格就是你應用表象我來指涉被你當作擁有所有精神屬性——比方說——在內感官中被展示——的虛構的我或實體e🙍🏿♀️,通過綜合內感官的雜多而得到的)。我們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使用任何特殊的、個別的第一人稱表象🧑🏼🍼。(我們僅僅擁有關於統覺的思維行為關於其自身從思維主體x中流出的反身性意識。)
然而,當我們開始綜合來自外感官和內感官的雜多之時,我們產生了一個特殊的、第一人稱的表象——比方說✍🏿🚵♀️,我之前提到過的表象M。當使用這樣關於所有屬於我們自身的雜多元素的第一人稱表象之時🧑🏻🦰,我們才能以一種真正的第一人稱的方式思考👋🏻,即:我思考“我看見了我面前的這臺電腦”。因此我們也認為,我們虛構性地設定了一個對於這個表象我的指涉,一個擁有所有雜多元素的實體e(經驗自我)。
根據我所支持的觀點,這一指涉物本身並不真的存在——真正存在的,是表象我。但這一表象我就其自身而言是轉瞬即逝的➡️;它在綜合過程中來了又去👨🏼🏫。並且那一表象的虛構性指涉物🏍🧒🏼,經驗的我💛,其自身也是飛逝而過的。這一虛構的指涉物就是我們用我們自身日常意識的“我”之思想所指代的東西(就像當我說“我看見了在我前面的這臺電腦”時)🎹。這一虛構的指涉物與思維主體x不是一回事🏹。並且那個未知的思維主體也並不進入我們關於世界的真正知識之中👩🏼⚕️,我們關於在時間和空間中對象的知識源自我們關於外部和內部世界雜多綜合的結果。相較而言🚊,當知曉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將知識也歸於表象我的虛構指涉物了。
以上的總結給出了我試圖在本書中重建的自我意識觀點的概貌。正如我之前所說的,我本人的觀點始於卡斯特內爾達關於“我”的論述以及霍威爾關於康德“我思”的論述,這個新的觀點也結合了某些早期的建構嘗試🦸🏼💆🏽♂️,這些嘗試在以上兩位哲學家那裏都不曾見到。我關於表象我的轉瞬即逝特征上的觀點與卡斯特內爾達的一致🧑🏼🏭👨🏽💻,但是我不將轉瞬即逝的經驗性的思維主體(在這個例子中✍🏿,那個叫“尹潔”的人)與其表象相等同🍫🥙。取而代之的是,我已經在這幅圖畫中加入了這樣的部分↪️,即卡斯特內爾達發展了這樣一個觀點——當我們使用表象我的時候,我們也在想一個虛構的東西。我們虛構性地思考,那一表象擁有一個指涉物🕢,那個表象指涉實體e🔳,盡管沒有這樣的實體真的存在♿️。
最後我要強調一下我在此處總結的觀點與克切的這一觀點吻合,即,我們只有通過那些統覺之行為才能得到思維主體x, 即那個產生統覺行為的東西。再者(這一點康德本人也強調了),因為那是唯一我們能夠得到那一實體的方式,我們關於那個實體的本性沒有任何知識,也沒有關於其如何產生其統覺性的行為的知識,等等♡。因此我認為我的觀點不僅僅抓住了康德本人建議的關於自我意識的觀點𓀋,也同時是至今為止沒有在文獻中得到過充分處理的觀點🎒。只不過我關於康德的一些觀點仍與當代康德學者發展出來的大部分康德理論較為一致。
在總結這一觀點的呈現的時候,我也應該強調下,有人也許會問基於什麽理由我們要接受這一理論的那些起點,即存在著一個不可知的思維主體x,這一思維主體產生出統覺行為從而啟動了以上描述的那整個過程🫚。即使思維的主體被引入作為我們不知曉其本性的某物(以及作為不是任何一類康德式經驗知識對象之表象的某物),那麽在我的理論裏究竟什麽理由使得我們能夠接受這樣一個主體呢?
作為回應🏊,我強調兩點✒️。首先🫦🔡,在本書中我試圖盡可能地重建康德本人的觀點👩🏽⚕️,我認為康德本人很明顯地接受了這類不可知的思維主體的存在📳。(確實,他認為他自己的整個對象框架需要接受這個主體的存在,那些對象經由外感官和內感官向著主體顯現🧚🏼🧂,然後經由那一主體綜合的、統覺的行為而被知曉,盡管這一主體自身不是康德式認知的任何對象🧑🏻🎤。)其次⚗️,似乎可能的是一個我的理論的一個更為極端的觀點可以被發展出來✋🏻,在這個觀點裏思維主體自身最終不被當作真正存在🫴🏿,而被當作在某種意義上是虛構的。如果持有的是這樣的觀點的話,那麽我們將不得不用來開啟的東西就是反身性的、統覺性的行為(我們意識得到這些行為的存在,經由我們對於其的產生過程)。那些行為以某種方式(也許以某種虛構的方式)引入了關於其自身的反身性的思維,這一思維就是他們自身源自一個思維主體x👩🚀。他們引入那一思維盡管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的思維主體x真的存在。然後我所描述的整個過程從步驟1到3都發生了。
如果要再為具體地發展和辯護這個觀點將會引起很多新的困難的問題。我本人不確定最後它是否能夠被很好地辯護🤸🏻,盡管我同情這個觀點👨🏼🎓,甚至認為其中有些版本是非常合理的。無論如何,基於以上強調的理由✍️,我認為極端的觀點不是康德本人的觀點,且細節性地探究這個觀點也超出了本書所能及的範圍,因此此處不再贅述🍕。它當然引起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議題,然而,卻是既哲學性的又歷史性的。(比方說🙏,它能與費希特那個被康德激發的觀點相關聯,即經由我思👇🏿,自我不知怎地“設定其自身”。)但是我還是將這一探索任務留待今後完成。
6.3 這個模型如何回應霍威爾的兩個問題呢?
如果有人還記得霍威爾(2006)在討論我思與自我意識時涉及的三個方面的話,那麽應該可以看得到我這裏給出的模型可以解釋:
首先,代詞“我”的索引詞使用,因為僅當第一人稱我的意識在一個人那裏達成的時候,他才能說出代詞“我”從而指涉自身,並且這樣的指涉是直接的🥈,即無需任何描述中介,因為它僅僅需要一個人經由他自身指向他自身,這就是一個反身性的自我意識🧘🏿♂️。
其次👨🏼🔬,在這樣的模型裏🤷🏼♀️,當使用的代詞“我”的時候,指向一個人自己也是免於錯誤識別的,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這一點。第一個是,不用依賴於任何識別行為,通過先驗統覺的綜合行為直接地指涉或挑選出那個思維主體e,因為它所產生來綜合直觀雜多的那個我之形式 🧜🏽♂️;第二個是,我之內容被歸於思維主體是僅當這同一個思維主體執行了那同一個統一化且使得我之內容(或相應的經驗認知)變得可能。換句話說🐾,自我意識被達至的方式決定了這個模型中的自我指涉並不需要一個額外的識別行為。
第三,在這個模型裏,對於“我”的直接指涉性使用不能被還原為、或分析為任何不受霍威爾那個規則(R)統治的術語之使用。規則(R)認為說出代詞“我”的說話者就是代詞 “我”指涉的人👨👩👧👦,並且這在我重建的模型中也是真的,因為僅當一個人能夠擁有他自己的第一人稱我之意識之時,他才能說出代詞“我”🆙,因此當他說出“我”的時候他肯定意圖指向他自己而不是其他人,這肯定是符合規則(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