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簡<五行>章句講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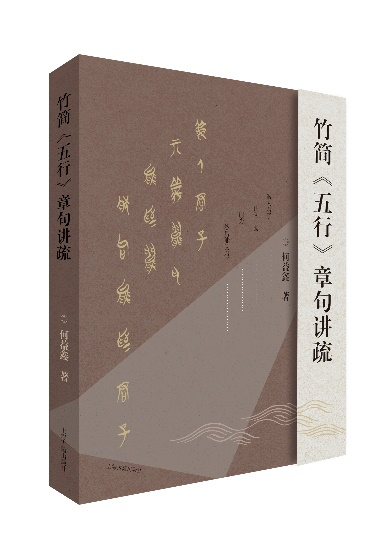
作者:何益鑫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4年1月
郭店竹簡《五行》作為思孟學派的核心文本💥,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出土、公布以來🏂🏼,諸多學者時賢圍繞《五行》做了大量重要的研究工作。本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以早期儒學的問題意識和發展線索為基本的理解背景🤸♂️,通過逐字、逐句🧔🏿♂️、逐章的分析討論,重新論定《五行》的內在旨趣、行文思路和思想要義👩🏼🔧。與前書《竹簡<性自命出>章句講疏》一樣,本書也采取了“章句-講疏”的寫作形式,以“導論”為綱領,以“章句”為根本,以“講疏”盡其義🧑🏼💻👩🏽🦲。
何益鑫,意昂3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先秦儒家哲學、早期易學。著有《成之不已:孔子的成德之學》、《成性存存🧕🏻:孔門成德之學的演進》、《竹簡〈性自命出〉章句講疏》👨🏽🏫、《<周易>卦爻辭歷史敘事研究》等↗️。獲評2019年第八屆“士恒青年學者”,2020-2021年度“上海社科新人”,上海市第十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學術新銳獎”(2023年)🛫。
導論🫲🏿:德的生成——子思《五行》篇的德行生成論及其思想史意義 1
《五行》章句 1
《五行》講疏 21
一、總綱 38
二、由仁而智聖以至於和 59
三、由聖智而仁以至於和 167
四、余論 283
引用文獻 291
後記 297
* 出於編輯需要,章節選讀部分註釋被省略,詳情請參見原文
聖之思也輕,聖之思🧏🏿♂️,謂聖之行於心術者🕧。聖者🔉,智之極🩳。輕,快也、易也。言神思悠然、倏忽而至🫘,猶“不思而得”也。輕非不長,以其流行之易🗝🖌,不假用力,若無為而然者也。○《荀子·不苟》:“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言操之熟乃輕耳🪃。輕則形,形則不忘🔠,不忘則聰,聰則聞君子道📸,聞君子道則玉音,玉音則形,形則聖👲🏽。聰者,聖之藏於耳也⏰。聞君子道,謂能於眾中辨識之也。更知其所以為君子道,知其為天之道👩🏻🍼,則玉音🧚🏼♀️。玉音,猶德音,有德者之言也🎨。至於玉音,則聖德成矣。
右第七章🖕🏼。言聖之思也,至於玉音而聖成。
本章是講從“聖之思”到“聖”的成形過程🤞🏽。聖從屬於廣義上的智,與上章所說的智有關系,又有區分。
第一句“聖之思也輕”。與前兩章相似,“聖之思”指承載了聖的意識活動,或者說聖德在意識活動層面的載體🪹。它的基本特征是“輕”。那麽,什麽是輕呢?帛書《說》解釋說:“思也者思天也🐎,輕者尚矣。”魏啟鵬說:“‘輕’有輕舉🤟🏿,飛升和上揚👩🚒、超越等含義。故帛書《五行》之帛書《說》得以‘輕者尚(上)矣’解詁。”常森說:“殆謂思考天道或者德臻於精熟之地就超出常人。尚,超越🤞🏼,高出🧑🏻🎓;《論語·裏仁》篇載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輕舉⇾、超越、高出🍎,都是與上下方位有關。要註意的是,一如仁之思的“清”、智之思的“長”一樣🏍,“輕”乃是“聖之思”的特征,而不應該是指向聖之思的對象📏。且從上下文看💂🏻,對象的凸顯至少要到“聰”的階段之後。故帛書《說》“思天”的解法🦥,與簡文本義未必相契。又,陳來先生認為:“輕本是指聲音的輕細而言,聖就是對聲音有敏感的聽覺的人🧞♂️,聖表示對再輕細的聲音也能聽到。”與前解不同🏫,這是從“聖”與“聰”的關系入手。不過,與前解類似的是🕺🏼,此說中的“輕”也是形容聖之思的對象(聲音輕細),而不是聖之思本身的活動特征。
龐樸先生指出🧈:“《禮記·中庸》所謂的‘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及《荀子·不苟》‘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可作“聖之思也輕”之解✍️。”相對而言,這一解釋直接以《中庸》和《荀子》為依據,其對輕的了解更為可靠🚴🏽。
故此,聖之思的“輕”,不是由於思的對象的差別,而是關乎思的精熟程度。思之輕,可以是相對於思之重而言。思之重,是費力思考而得的🧚🏽♂️;思之輕⚠️,則是“不思而得”🧑🏼🚒。《中庸》所謂“不思而得”,即聖之思也輕;與之相對,“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而得𓀜,便是人之思也重👨🏻🦯。《荀子·不苟》所謂“操之”,是用心操持🦶,思之重者也;“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得之而獨行之後,思之輕者也。伊川答橫渠曰🏌🏽♀️:“所論大概,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答橫渠先生書》)這一說法也可以借以說明問題。伊川說橫渠的論說,多是苦心極力的考索🙆🏽,是思之重者👩🏼✈️;而與之相對⛸,來源於“明睿所照”的自然見解,則是思之輕者。
因此,思之重或思之輕的差別🧛,主要不在內容👨🏼🦰,而在思維的過程👩👩👧:費力或不費力𓀂,有跡或無跡💆🏿♂️,有意或無意⛰。如果說,智之思的“得”,必須經過“長”的階段,亦即經過一個在時間中持續的思維運作的過程🌶;那麽👨🏽🔬,“聖之思也輕”,似乎是指不需要時間過程的直接的把握🧳,近似於一種理智上的直觀。其實🙆🏻,可能並不是真的直觀,只是其思維的過程隱沒在了結果的瞬間呈現之中,只是作為此結果的一個內在結構而存在。而這一過程本身🧑🏽🦲,在思者本人這裏,甚至都沒有進入到自覺的意識狀態🛏,故有一種不期然的Ⓜ️、無意的、不思而得的體驗。
接著是“輕則形”。這裏的“形”,顯然要與“形則聖”相區分,它不能理解為德之行的成形。那麽,這個“形”是什麽意思?學者基本上沒有給出有效的解釋。所幸的是,從本章開始,帛書就有對應的帛書《說》內容了。關於這一句,它有很多的發揮。
“聖之思也輕”🦷。思也者,思天也;輕者,尚矣。“輕則形”🙌🏻。形者,形其所思也。酉下子輕思於翟,路人如斬🌱。酉下子見其如斬也,路人如流🙋🏻♂️。言其思之形也。
把“聖之思也輕”從內容上解釋為“思天”👨🏼🏭😸,未必是對此句最有針對性的、最直接的解釋,這個之前我們已經說過。不過,帛書《說》對“輕則形”的解釋很值得參考👩🏽。“形”即“形其所思”,舉了一個酉下子的例子。這裏的“酉下子”🚴🏽♀️,一般認為是柳下惠。《論語》有三章(四次)提到他,《孟子》則有五處(六次)提到他,並稱他是“聖之和者”。但此處的故事👏🏻,卻不是很好理解👩🏻🦼➡️。我們一點一點來看。
何謂“路人如斬”👳🏽🙆♀️、“路人如流”🧘♂️?整理者指出:“斬流皆喻行止之態,《商君書·賞刑》述晉文公將明刑以親百姓,‘三軍之士🕋,止之如斬足,行之如流水,三軍之士無敢犯禁者’。”此說可從。所謂“路人如斬”,說的是路人好像被砍了腳一樣一動不動🧚♀️👍🏽;所謂“路人如流”👰♀️,說的是路人行走穿梭沒有停頓🕵🏽♂️。
何謂“輕思於翟”💅🏻?魏啟鵬說:“於翟,當與《四行》所謂‘其事化翟’義同,‘於’,魚部影母🦸🏻♀️。‘化’🎽,歌部曉母。其韻魚歌通轉,古所常見;影、曉古為喉音清聲旁紐𓀃,其聲同類,故‘於’之與‘化’音近。……‘於翟’同‘化翟’,化施變易也🏄。”所謂《四行》,指帛書《五行》經說之後的一個文本,有人認為是《五行》的後敘。其中有這樣的說法🔟👩🏻🔧:“聖者知,聖之知知天👩🏻🎤,其事化翟🧜🏿。”魏啟鵬解釋說😼:“化翟通‘化易’🏊♀️。……《荀子·君子》:‘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謂變化移易也👍🏽。《孟子·盡心上》🤘🏿:‘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哉🦹♀️!’《盡心下》🔗♘:‘大而化之之謂聖。’可與‘其事化翟’之意互相發明。”參照魏氏的解法,則此處“輕思於翟”可以理解為,柳下惠的輕思已然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那麽♾🦻,串起來又怎麽說📷?由於柳下惠是“士師”(獄官)🍘🚴🏼♀️,故整理者認為:“路人讀為累人⚁,指系囚💆🏻♀️。”順此🧑🏻🏫,魏啟鵬說:“路人如斬,謂累人皆從柳下惠之斷獄也。……路人如流🖕🏻,即謂累人亦從柳下惠之刑德教化也。”這一說法似乎不妥。即便“路人如斬”和“路人如流”可以這樣解釋,問題是🧔♂️,這與“酉下子輕思於翟”有什麽關系?與“形其所思也”又是什麽關系🎛👮🏽♀️?“酉下子見其如斬也”,為何要強調是柳下惠的“見”?說的還不夠圓滿🧘🏽♀️。
常森認為,這句話“殆謂柳下惠精熟地思考於翟而忘懷其他🛣💝,以至於認為行走的路人像被斬去腳一樣靜止,——這只是柳下子見路人被斬去腳一樣靜止,路人其實像流水一樣在行走🦏。句意是說對對象的高度集中🫸🏼,超越了對其他事物的關註🧴。”此說除了把“翟”解作鳥,認為柳下惠是在專心思考鳥的問題,這一點令人費解之外,大體還是抓住了一些要害的。“路人如斬”,不是真的路人如斬🧎🏻♂️➡️,而是柳下惠思中所見🚫、見其如斬;真實的情況,卻是“路人如流”👩🏼🍼🥇,路人從來沒有因為柳下惠的思,而停止過穿行的活動。常森說,這句話的主旨是突出柳下惠由於思考高度集中,超越了對其它事物的關註。這一解釋,無法落實“形”的意義。從原文看💂🏻♂️,“形”無疑是此中的核心概念🏌🏽。帛書《說》“言其思之形也”🤵🏽,在語脈中是作為故事的總結。這表明,柳下惠的例子,所謂“路人如斬”、“路人如流”,最終都是為了說明“形”的。所以✌🏼,問題的關鍵,是“形”與“見其如斬”兩者之間的關系的理解。
此中的突破口🤷🏿♂️,是“路人如流”的事實與柳下惠“路人如斬”的所見🖕,這兩者之間的鮮明對比。柳下惠之思的特殊之處就在於👩❤️💋👩,現實中路人穿行在他的世界中,就都好像停止了一樣👩🏽🍳,定格在那裏。這樣的思,實是一種直觀的⛄️、整體的把握能力。我們一般對於事物的觀看和了解💕,總是有一個順序的,從一點到另一點,從局部細節的觀察開始漸漸形成整體的把握,這個過程是需要時間的🙆🏼♂️。對於靜止的事物,尚且這樣;對於運動的事物,更加如此🤵♂️。事物如果運動過快,很可能在我們對它形成整體的把握之前,就已經消失不見了👩🏻🦯➡️。在這個故事中🦂,川流不息的人群正是運動的事物。對它的觀察,普通人只能抓住其中的部分細節(比如看到了其中有一個奇裝異服的人,或者看到一個異族人🕉,或者夾雜著一個鬧哄哄的小孩),即便給你時間不斷地觀察,也是很難形成完整的把握🧑🏼⚕️,看清楚全貌的🚴🏽♂️。因為它一直在動◼️🤾🏻♂️,動意味著新狀況的不斷出現,具體的事態稍縱即逝;與此同時👷🏿,我們觀察它、思考它的過程都是需要時間的🤏,幾乎不可能把握某一個特定時刻的整全面貌。然而,對於柳下惠來說,流變中的事物,看上去是靜止不動的。不是說真的靜止不動🔢,或者柳下惠有時間定格的能力,它其實是說柳下惠可以在每一時刻沒有錯漏地同時把握路人的全部事態。當然🎳,本質上🧑🏽🍳,這種能力取決於柳下惠具有的超強直觀和綜合把握的能力。帛書作者認為,這是柳下惠“聖之思”出神入化的表現。
電影《頭文字D》裏面講到一個現象,拓海在秋名山上送豆腐Ⓜ️,一年又一年,他發現周圍的世界在漸漸變慢,而實際上,是他的車開的越來越快😶🌫️。拓海為什麽會覺得世界很慢?因為盡在他的下意識的掌控之中,不需要有意識的思考就可以操控👩🏼⚕️,沒有新的情況讓他感覺到自己的意識活動。與之相反的是,當我們剛開始駕車的時候,覺得道路上的事態變化的好快。為什麽會覺得快?因為對於新手而言▶️,每一種路況都是經過觀察-思考-操控的這一復雜的過程而實現的。且對交通事態的觀察,又是一個點一個點👒,通過註意力的持續轉移而拼湊出來的👩🏻💼。所以總是會覺得👨🏻🔬,路況更新太快🙇🏿♂️,要註意的點太多👩🏿🍳,一個腦子不夠用。設想🧑🏻🎨,如果大部分的路況都很熟悉了,都在下意識的反應之中,那麽🤦🏿♂️,腦子就會留下足夠的時間🦒,讓你處理可能偶然發生的新情況。進一步,如果一切都是熟悉的路況,通過肌肉的習慣性記憶就可以應對,那麽,此時就會覺得整個過程是不需要意識活動參與的,只要一瞟就能洞悉全局。在此一瞟之中🏌🏽,時間近乎是停止的,因為它幾乎已經不需要在意識層面的接受和綜合的時間了。拓海達到的是第二重境界,時間慢下來🐏,但還沒有停止。他只是熟悉了那條秋名山的盤山路,若換成其它地方的路🏐,他還是需要經歷一個漸漸熟悉、漸漸自如,以便讓時間漸漸慢下來的過程。而柳下惠達到了第三重境界,他對事物的觀察和理解近乎直觀,瞬間把握全局。似乎世界對他來說可以隨時停止📟,就像照相一樣🦵🏻,待人細細回顧其中的細節。
帛書《說》為什麽會舉“路人如斬”的例子呢?這倒確實可能與柳下惠的士師身份有關。士師斷獄🤵🏻♀️,最重要的是細節的觀察和把握🦻🏻⚀。或許柳下惠非常善於把握事態與細節,只要一過目,悉在掌握之中。故帛書《說》作者以他為“輕思化易”的代表。
如果進一步打開腦洞,柳下惠見“路人如斬”的例子,似乎也可以從比喻的角度說✩🚋。“路人如流”指一般的思的活動,它是一個前後相繼的歷時性運思的過程🍔,其結果要在進程全部完成之後才能呈現。相對而言✖️,“路人如斬”指一種無時間性的直觀把握👨🚀,思的始與終一時呈現,沒有了思的過程。由於思路急速鋪開,以至於感受不到意識活動的時間性,則思者最終的感受只是刹那獲得、瞬間完成,此則《中庸》所謂“不思而得”🩸。但它不是沒有頭緒的孤零零的一個終點,若要反思其思路之所由🪕,又可以歷歷在目地呈現。換言之👨🏻🦯➡️,聖的不思而得,其實不只是一個結果,更是可以“直觀”從思路到結果的全體。一個本來要在意識活動的歷時過程中逐步展開的東西,變成了一個在空間中平面鋪開🧑🏿🏭、直觀可見的東西。就好像不斷發生變化著的穿梭的人流,定格為一幅靜止的畫面。平鋪的東西,可以同時直觀到全體,這就是“形其所思”(歷時過程圖像化)😲。故“形者🧎♂️➡️,形其所思也”🏸,形就是“所思”在“思”中的呈現方式。這個意義上的形,與《樂記》“心術形焉”的“形”接近。
以上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與帛書《說》的原文更加貼切,可能更加接近帛書《說》作者的用意。順此🤥,這一句中“形”的意思,簡單來說就是聖之思對於事物或者對象的把握方式。智之思要經過一個歷時性的復雜的運思過程才能“得”,這個“得”指的是對於對象的認知和把握💂🏽♀️,故曰“長則得”;與之相比🦸🏿♀️,聖之思對於對象的理解是近瞬間達到、近乎直觀的,不需要意識活動的過程,非常輕易的🛤,故曰“輕則形”🔪。當然,“長則得”也可以理解的很深🚣♀️,故此處“得”與“形”並不強調內容的差別,而是凸出了過程的區分。得強調結果🕵🏽♀️,形強調綜觀🧚♂️,基本意義是一樣的。
得之後🅰️,都不會忘記,故曰“形則不忘”。智的不忘,是因為新事物在既有的意義脈絡和知識背景中獲得了理解,得到了條理化、系統化的整合。聖的不忘,說到底也是由於內部的一貫性🦆,只是它的一貫性更為圓融和無跡。故對新知識的接受🧑🏿🍳,無需理解和運思的過程,自然融入。
在此⛄️,帛書《說》雲:“‘形則不忘’🙏🏽🧖🏿。不忘者🧑🏽⚖️,不忘其所□也,聖之結於心者也。” 根據上下文🆖,缺字當補為形🤰🏼。聖之思的活動,對於事物而言也是一種表象活動🎩🫥。故“所形”是指聖之思所表象的對象,或者說是聖之思對對象的表象結果。這種表象活動🤵🏼,不僅僅是一種呈現活動👩🏻🦱,更是一種理解活動。所以,“不忘其所形”,意思就是不忘記對事物發生過的理解。
而這種能力,從根源上源於內心既有的聖德,從結果上它的積澱又反哺了後者,構成了下一次的聖之思的活動的基礎⏩,故曰:“聖之結於心者也🦸♂️。” 結👉🏻,謂締結🧏🏽♀️、凝聚。一般而言,聖的意義💆🏼♀️,與卓越的聽覺能力相關。但聖聰,不僅僅是感知的能力🤦🏻,更是認知和理解的能力🛷。這種能力,本身是要以學者內心的義理體段為前提的。故聖之思之所以輕,源於義理之精熟📴🧑🏿✈️;形則不忘的結果🧑🎓,又反過來充實之🤣,兩者互為因果🏊♂️👵🏼。這一點與智是相似的🏇🏿🏂🏻。池田知久認為👇🏼:“此句是講,在人類的‘心’中先天地自然地被賦予的‘聖’🫨,是‘思’、‘形’這樣一種後天的人為的努力的結果,再返回本來的樣子,成為‘結於心’而‘不忘’的狀態。”按,在《五行》中🥚,聖或許有天生的因素,卻不是一種完全天生的德性。所以,才會有聖這種德之行的形成問題。聖的形成,或者說它在內心的凝聚,源於聖之思的意識活動🏋🏼♂️🧭。這個活動是人為的,但又不像是人為的🧑🏼🚒,因為它似乎是直觀的、自然的,淡化了“人為的努力”🍒。由聖之思自然而然的活動,得到新的理解反哺🧔♂️、積澱於內心,成為下一次聖之思的基礎,如此反復👌🏿,則聖之思越發的輕⚛️,越發不思而得,這便是“聖之結於心”的過程。
以上是聖之思的內在活動🕘,尚未涉及到感官功能。接下來是表現於外的實現活動,依托於感官。
“不忘則聰”。儒家之前,聖🫔、聽👨🏻✈️、聰三者已有穩定的關聯🍝。龐樸先生說🌉🤴🏻:“《書·洪範》:‘聽曰聰🥛。’古佚書《德聖》🙅♀️:‘聖者👳,聲也🪵。……其謂之聖者🐋,取諸聲也🥕。’《文子》👩🏼🦰:‘聞而知之,聖也𓀄。’(定縣漢簡1993)《白虎通·聖人》:‘聖者🪜,聲也🥟。……聞聲知情。’又郭沫若《蔔辭通纂考釋·畋遊》:‘故聽、聲🧀、聖乃一字。其字即作𦔻,從口耳會意🧔。言口有所言,耳得之而為聲,其得聲動作則為聽。聖、聲、聽均後起之字也。聖從𦔻壬聲,僅於𦔻之初文符以聲符而已🤫。’”實際上👩🔬,諸說關於聖、聽關聯的論述,需要作出層次的區分。第一層意義上的聖💏,與聽覺敏銳相關,“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能力和素質”🧖♂️,如郭沫若所說;第二層意義上的聖則是作為德行的聖🙏🏿,如帛書《德聖》(魏啟鵬命名為《四行》)、《文子》等所說👨🦳。作為“德之行”的聖🐈,無疑是後一種🏌🏼♀️。
故帛書《說》雲🙆🏽:“‘不忘則聰’🌼。聰者🍶,聖之藏於耳者也。猶孔子之聞輕者之擊而得夏之盧也。”聰是“聖之藏於耳者”,也就是說💤,聰是聖在聽覺器官上的表現🧛🏼♀️。在這一邏輯中,聰不是獨立的能力,它取決於內在的聖🙄。結合“不忘者……聖之結於心者也”的解釋🍀,則“不忘則聰”是說以結於內的聖心為前提🧑🏽,然後有聰。故此處的聰🦶🏼🪙,就不僅僅是一種敏銳的聽覺能力了,而是以內在心德為基礎的“聽覺-分辨力”👈🏽♠︎。
帛書《說》的後半句𓀉,出典未詳。有三種猜測🪁。整理者說,輕讀為磬✅,盧讀為虡🏛,是懸磬的架子🏃♂️。意思是說,孔子聽人擊磬就知道架子是夏朝的架子。龐樸說,輕者疑輕呂之誤,輕呂,劍名。夏之盧或為夏啟劍。意思是說,孔子之聞輕呂之擊而得夏之盧🧑🏼🦰。魏啟鵬說,夏之盧即夏之搏🛼,搏之聲也輕微。孔子聞輕者之擊而得夏之搏,殆寄其向往有夏,推崇大禹之意。三者都不能在傳世文獻找到典故出處👰♀️,但相較而言👩🔬,第一種可能更為合理。
《晏子春秋》記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景公為大鐘💅,將懸之🍭。晏子🛟🫃🏽、仲尼🦈、柏常騫三人朝➔,俱曰👷🏼♂️:‘鐘將毀🧞。’沖之,果毀👏🏿✊🏻。公召三子而者問之。晏子對曰🙅🏻:‘鐘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禮🤡,是以曰鐘將毀。’仲尼曰👨🏿⚖️:‘鐘大而懸下,沖之其氣下回而上薄,是以曰鐘將毀。’柏常騫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勝於雷🧑🏿🦳,是以曰鐘將毀也👸🏿。’”這一則記載很可能出於後人的演繹。但就這一記載而言,孔子從大鐘懸掛的位置,推論回聲容易使鐘發生過渡震蕩(共振)👨🚀🐮,從而推定了此鐘將毀🧑🏿🍼🌂。但問題是,一個鐘的共振頻率取決於很多條件,除了懸掛高度之外還與自身的厚度、大小有關。若果有其事,更有可能是孔子已經聽出了鐘聲中的共振⛓️💥,從而作出了這一判斷。後來在鐘的頻繁使用中🏄🏻♀️👏,果然毀壞了。這就取決於孔子音樂聽覺的敏銳,以及樂理的精通。
如果以上事件是可能的,那麽👩🦽➡️,通過擊磬的聲音而判定架子的年代也應該是有可能的。因為一個架子,至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其年代的特殊性🦞:其一,架子的型製🤹🏿,不同的年代架子的規製或有不同🧑🏽🍼;其二,所用木材🛜,不同年代慣用的木材可能不同🧖🏼;其三,年代不同導致木材的物理性質(如幹濕度)和聲音特質(共振頻率)發生變化,這一點只要從斫琴的用料選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四,架子上的勒痕深度,改變了磬與架子的接觸面和接觸程度,也會影響音質。這四者的差異,或多或少都會表現在擊磬的音質上🧑🏻🦯。綜合以上因素,至少從理論上,是可以從擊磬的音質而判定架子的朝代的。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這一點(就如不是每個人都能聽出一把古琴用的是老料還是新料),但孔子無疑有這種能力。故帛書《說》舉了這個例子來說明“聰”🧒🏽。
下一句“聰則聞君子道👩🌾。”以上對“聰”的解釋,還沒有特別凸顯道德的意義➜,此句揭示了這一點。本章的“聰”,可以包含寬泛的含義,但主要還是指向道德上的識別、理解和判斷力。故所謂“聞君子道”👩🍳,不只是聽聞君子的學說而已,更主要的是聽了之後能夠識別出“這是君子道”;並且知道君子道何以為君子道之故,所謂“聞君子道而知其為君子道也”。換個角度說,聽到的人可能很多🥕,但唯有聖之思發展到這一步的人,才能真正識別出君子道、理解君子道之為君子道🏈。這就絕不是感官聽覺的問題了,跟是意味著道德上的敏銳🐐、洞察、理解和判斷。
帛書《說》解釋說👩🦯:“道者,天道也🤞🏿,聞君子道之誌耳而知之也。”誌,記憶。知👩🏼⚕️,理解🛥。本章簡文只是說“君子道”,帛書《說》則直接以天道解之。其實😕,君子道在這裏應是指孔子思想為代表的儒家之道👇。《五行》作者(子思)認為,儒家的道是合乎天道的,或者說是與天道相通的💇🏿。在此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道者,天道也”;就如《五行》第1章“德,天道也”🏘♒️,也主要是從兩者境界的相通性而言的一樣👩✈️。但這並不意味著君子道與天道是完全等同的,適當的區分還是必要的。根據第17章的表述♐️🧑🏻🦱,聖人確實是“知天道”的。不過,這裏的關鍵在於,聖人所知的,作為指令的發出者或規範性的最終根據的“天道”,與以儒家學說的形式表達出來的“君子道”之間🔏,到底是一個什麽關系。我想🧑🏻🌾,就子思而言🙄🛍,他對天道的領會、對聖人的領會,以及天道與君子道的一致性的了解,最明顯表現在《中庸》關於“誠”的學說以及相關表述中⚗️,比如👈🏼:
《詩》雲:“維天之命5️⃣,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所謂“天之所以為天”,也就是天道之為天道的本質,在於“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文王之所以為文”,聖人之為聖人的本質,在於“純亦不已”。兩者是內在一致的✊、相通的。君子道之為君子道與天道之為天道的一致性,意味著對君子道之為君子道的認知🧑🏫,實際上包含了對天道之為天道的確認。在此意義上,知君子道之為君子道,也就是一種意義上的確認天道👊🏽、知天道🏌🏻。因此,《五行》所謂“聖人知天道”,或許主要是通過君子道的理解而透顯天道的本真,而不是由特異的聽覺能力接收來自上帝的聲音👩👧👧。
接下來“聞君子道則玉音”。玉音🛀𓀃,原指玉磬之音。第9🧑🦳、10章說提到“金聲而玉振之”🧑🦰,古樂必始於金聲💗💁🏽♂️,終於玉音📦,以玉音能收之故☸️。此處,“玉音”是說聖人之“天音”🦛。魏啟鵬說🦈:“簡文之玉音🫳,猶德音也。蓋《五行》篇以德為天道,知天道為聖🏋🏽,又以‘玉音,聖也’。故知玉音乃象征知天道者、有德者之音🛌🏽。參看《國語·周語下》載伶周鳩曰:‘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韋註:‘中德,中庸之德聲也。中音,中和之音也。’)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人以寧,民是以聽。’又,《國語·楚語上》🧦:‘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心類德音,(韋註🏓:‘類,善也。’)以德有國🍖。’”在《詩經》中💸🤳,“德音”出現了12次𓀈。鄭玄有“恩意之聲”“教令”“聲名”“先王道德之教”等不同解法。在《禮記》《荀子》及漢人文獻中🧑🏻🦽➡️,玉音一詞也經常出現🤵🏼👉🏽。如“其德音足以化之”(《荀子·富國》)、“厚德音以先之”(《王霸》)等。本章的 “玉音”📼,與聞君子道有關。且從“玉音則聖”看,這一階段意味著聖德的完成。故這裏的“玉音”👨👩👧,應是指聖人之言,或出於聖德的言語。
關於這一句,帛書《說》解釋說✌🏽:“‘聞君子道則玉音。’□□□□□□□而美者也,聖者聞誌耳而知其所以為□者也🚵🏻♀️。”後一個缺字,整理者釋為“物”。池田知久參照帛書《說》“見賢人而不色然,不知其所以為之”💂🏼,補“之”字👨🦼,指君子道👲🏽。可從🐝👱♀️。前面的缺文也有爭議。池田知久據後文“□□也者,己有弗為而美者也”🫃,補“玉音者己有弗為”,應該是不合適的🤶🏼。彼處“己有弗為而美”是形容德的👶🏻,而本章即便到了“玉音”,與德的完全實現還是不同的🦾。這句話🖋,雖然不知道怎麽精確地補充,大義還是清楚的。既然說是“玉音”,則闕文一句應當是說聖者出言之美👰🏻♂️。至於為何能出德美之言,是因為聖者聽聞、記住了君子道,並且深切地理解了君子道之為君子道的原因🧗🏼♀️,所謂“聖者聞誌耳而知其所以為之者”。
從“聖之思也輕”開始,經歷了“形”“不忘”“聰”“聞君子道”,到了“玉音”的階段,說明聖之結於心已經完成,聖這種德之行已經內在成形,故曰“玉音則聖”🦣。
從以上兩章來看,智與聖雖然都屬於廣義的智,區別還是很明顯的。最基本的不同是,智之思是長,聖之思是輕。前者是歷時性的🏭、過程性的;後者幾乎是瞬間達到、近乎直觀的🛶。從對象或內容說,智的主要任務是識別賢人,理解賢人之為賢人的德👩;聖的主要任務是識別道🕢,理解君子道之為君子道,並且契會和確證天道🕺🏼。比較智與聖的形成過程🤱🏼,在“不忘”以前,都是內在的運思、理解👨🏽、記憶活動,此後才區分為“明-見賢人”或“聰-聞君子道”。同樣都是理智德性𓀐,為何會聯結到不同的感官🏋️?又何以要建立對象的區分?智難道就不能有聽覺的參與🦵🏼,並且無法了解君子道了嗎?聖難道就不能有視覺參與,並且無法鑒別賢人了嗎?事實上,對於賢人的了解和識別,不僅僅是通過視覺,更要依據他的言談🕛💓。所以❌,“明則見賢人”的見,其實不能具象地理解為視覺上的看見。同樣的🚵🏼♂️,對於君子道的認知,也不僅僅是聽覺問題,很多情況下也需要文本的閱讀乃至聖賢的示範。所以🤸🏽,“聰則聞君子道”的聞,也不能具象地理解為視覺上的看見🙋🏿。
當然🐳,明與智,聰與聖,在先秦時代的一般的了解中就有親緣的關系。不過,我想問的是🤛🏼,除了這一層因素之外,《五行》把智、聖分別對應到見、聞兩種感官,是否還有思想的必然性🧑💼👇🏿?
有兩個方向或許是值得考慮的:一是認知的方式🐻,二是認知的難度。從認知方式來講,見的對象是有形的,聞的對象是無形的🐜。理解賢人可以通過長期的觀察🤭🗺、交流和思考🥙,由感性的把握漸漸上升到理性的理解。理解君子道,唯有借助於聲音和文字(文字也要講出來或讀出來,根本上還是聲音)➝,沒有其它可視化的途徑。聲音和文字的一個基本特征,是歷時性。信息的接收是歷時的,接收之後再領會意義,又是一個復雜的抽象思考的過程✋。聖的不同在於🤙🏻,對聲音的接受及意義的領會是瞬時發生的,不需要過程和時間🍳。它可以達到一種“意義的直觀”。好像一個歷時性發生的東西,瞬時平鋪開來,以一種可視化的形式(意義圖像🤸🏻,時間的空間化)得到了把握。帛書所舉的“酉下子見路人如斬”的例子,就說明了聖者在表象活動中達到的意義直觀🕐。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還可以看一下孔子🚍。子曰:“六十而耳順🛑。”(《為政》)耳順,一般解為“聲入心通”🧘🏽。“聲入心通”🥧,意味著聲音與意義的瞬間轉換🧖。孔子可以當下領會聲音的意義,不需要思考的時間🖕🏽,也沒有任何的遮蔽。過程如此迅捷、徹底、且自然,這是孔子六十歲達到的境界。實際上,孔子還不只是“意義直觀”🂠,有時還會因意義的領會而表象為具體的形象。如孔子向師襄學琴,經過了“得其數”“得其誌”的階段之後,“(孔子)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誌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雲文王操也。’”(《史記·孔子世家》)學一首曲子,不但可以把握它的思想意趣,還能體會作者的生存意態和儀容風貌➰,並由此判定曲子的作者是文王。其判定🤴🏻,還被師襄子證實。可見,孔子的“聞而知之”🏌️,到達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以此反觀《五行》,則“輕則形”的形,不僅僅是關於所思內容的意義直觀,還可以包含意義的具象直觀(人物化、情境化、圖像化)。
無論是意義直觀,還是意義的具象化,某種意義上都是向空間或視覺把握方式的轉化𓀚🙏。從人類的思維特性來講↔️,綜合的把握(直觀)往往具有空間化或視覺化的形式。因此,相較於“見而知之”👩🏽✈️,“聞而知之”多了一個抽象事物視覺化表象的環節。後者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過程。
從認知難度來講,有人真實地在你面前,言行舉止各個方面都可以觀察⇨,可以與他有豐富的🌡、立體的交流與互動(包括情感互動),理解起來當然容易一點;君子道是以語言和文本的方式表達的抽象的東西👹,理解起來當然困難☕️。好比同樣是文王,是文王身邊的人更容易理解文王呢?還是千載之後的人🪨,憑著關於文王的記載和傳說🗃,更容易理解文王呢?顯然是前者🙎🏼。故下文第16章說🎑:“見而知之,智也;聞而知之,聖也。”後來👏🏽,孟子以“聞而知之”說湯🎇、文王、孔子,以“見而知之”說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等(《盡心下》)。雖然不能說“禹”不是聖人,但相對而言,前一系列的人物更具有歷史中繼的意義🧓🏽。
要之,智更傾向於具象🪁,故以“賢人”為對象🥗,以“賢人之德”為理解的目標✉️,此“賢人”可以說是道德的人格化的表現💂🏿♂️🏃🏻♂️;聖更傾向於抽象🙍🏽♂️,故以“君子道”為對象🏂,以“君子道之為君子道”或“知其天之道也”(帛書《說》)為理解的目標🧙♂️,此“君子道”或“天道”乃是道德自身。具象以視覺為代表,抽象以聽覺為代表。這或許就是《五行》作者將智、聖分別與明➙、聰對應的一個原因。具象的東西有其自身的邊界,超出這個邊界,智的運作就會很吃力🈯️。聖由於其思維的特殊性🧑🧒,能直接把握更為抽象的東西,或者說能透過具象事物而上達天道(知天道),這是智所不及的🙇🏼♂️。《五行》把對於天道的理解以及境界上的契會,作為成德的最終階段。有沒有聖,也成為了“善🧜🏻♀️,人道也”與“德,天道也”的根本區別。